|
内容提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1704号圆明园地盘图是迄今仅见的唯一一张完整记录乾隆朝圆明园盛况的绝世孤本,也是现存圆明园图档中绘制年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表现内容最丰富、记载变化最全面的国宝级珍贵档案。该图极有可能是清代著名样式雷家族的第三代传人——雷声徵执掌清宫样式房楠木作事务之时,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前后绘制的圆明园本部平面。此后该图一直作为档案图纸使用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几乎囊括了一部全盛时期圆明园的变迁史,是研究圆明园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发展变化的最权威、最完整的档案记录。
关键词故宫博物院1704号圆明园地盘图乾隆朝 传世孤本 雷声徵 样式雷家族
一 概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704号圆明园地盘图(以下简称1704圆明园全图)是一幅极为罕见的乾隆朝图纸,也是迄今仅见的唯一一张全面反映盛时圆明园风貌、记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圆明园变迁史最权威、最完整的国宝级档案。
原图纸本,横长1761.2 厘米,纵高1311.5 厘米, 墨笔绘圆明园山形水系及各建筑组群,无建筑景名、题额,无年款[2]。图中建筑柱网平面、廊房、墙垣、台基用界尺墨线绘出,山水轮廓与叠石、道路、水渠分别以曲线、墨点或渴笔皴擦表现,水面部分及土山略施淡彩。图纸左上方标注北苑墙长520丈, 根据制图比例折算,知此图是以图上一分表示实际一丈的1:1000的地盘画样[3]。图上多处粘贴、涂改,彩墨渗渍,陈旧斑驳,仿佛历史岁月留下的斑斑印迹。右下角钤有原中法大学收藏印,20世纪50年代收归故宫,此后一直庋藏于故宫图书馆〔图一〕。
圆明园创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四十八年蒙玄烨赐名,原本是皇四子胤禛的私邸。胤禛即位,将赐园扩展为皇家御苑,自雍正三年起园居听政,以后沿为惯例,遂使圆明园一跃而成为与紫禁城相比肩的政治文化中心。
雍正皇帝勤于政务,同时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除祭陵外极少离开京城,所居以圆明园为最久,对圆明园的经营也最上心、最到位。至十三年去世之时,圆明园已是一座结构无比精密,内容备极丰富的大型皇家山水离宫。正如乾隆御制《圆明园后记》所云:“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洵为集锦式平地造园艺术的杰出典范。
乾隆九年(1744),圆明园的增补完善工程告一段落,实乃对于雍正朝圆明园的全面总结,弘历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序,敕命唐岱、沈源合笔绘成《圆明园四十景》巨帙,成为圆明园、也是清代皇家造园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里程碑。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初度南巡后,又在以圆明园为代表的北方皇家园林中兴起了写仿江南名园、名胜的新高潮,至乾隆五十年(1785)方告基本结束。 故宫1704号圆明园全图反映的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圆明园本部的盛况,它全面记录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处于巅峰时期的“万园之园”的全貌,具载一代名园跨越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演变历程,称之为圆明园建园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或许并无过分。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之役,雷氏家族贮存于海淀故宅的早期档案图纸、烫样毁于一旦。就目前传世图档来看,大都为道光、咸丰年间的改建工程底稿,嘉庆旧图已然鲜见,乾隆原图则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故宫图书馆的这张有确切纪年可考的乾隆朝圆明园全图能够得以保存至今,实在堪称奇迹。该图弥补了圆明园研究史上的诸多空白,使种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据以澄清,其在学术和文物方面的双重价值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 年代考证
鉴定1704号圆明园全图的上限与下限,即初始绘制时间和后期重复使用的不同时间段,需要对原始图底、粘贴图层、白粉覆盖处分别对待。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对底层图纸纪年的准确判定。


圆明园作为清代皇权的象征和五朝皇帝最重要的离宫,随世代的移易和园主人的更迭,许多园景建筑也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纵观流传至今的样式雷档案,凡有详尽平面图像的景点、景区,大都涉及后代的重修或改建方案,除去少部分“准底”——即标准图纸的副本之外,绝大多数均为设计草图或测绘底稿[4]。其上标注的地名文字、尺寸数据虽失之潦草,却往往透露出前者不具备的工程细节或历史信息,补阙拾遗,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前者。1704号圆明园全图正是这样一幅曾被样式雷家族反复使用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珍贵稿本。
故宫1704号圆明园全图是一幅“百衲衣”式的乾隆朝老档,其中粘贴、涂改近百处,一些著名景点均呈现两层图纸重叠的现象——表层为修改图,底层为原图,两层图纸之间清晰显现出改建前后山水、建筑轮廓的差异。传世样式雷图档中,这类图纸不在少数。清宫样式房设计师为减少制图工作量在前代图纸上修改,或是将等比例、等大小的改建方案覆盖在原图相应位置上的情况十分习见,此乃手工制图时代绘图人为节省时间精力,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而惯用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工作方法,无意中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只要使用科学方法,将涂改、粘贴部分还原,即能得到旧有的图像信息。通过对1704号全图各修改图层内容的甄别,可知该图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更替,其全面性、完整性与复杂性在目前所见同类图纸中独一无二。
根据修改方案势必出现于成图之后的常理,判定1704全图初始年代的第一步可以采用“揭裱法”与“还原法”——亦即使用电脑技术处理,将各个时期的修改图层全部删去,同时恢复白粉覆盖处的底稿,使乾隆朝的原始平面得以显现。
清代御苑的创建、改建工程大都有年代可稽考,特别是御园圆明园,幸有乾隆九年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为时代坐标,画面、图纸两相比照,同时参校清五朝皇帝的御制诗文,证以内务府相关档案以及其他文献资料,条分缕析,不难把握园中景物变迁的清晰脉络。弘历继位后频繁出巡,十六年南巡后大量引进江南名胜,增缮不断。略去小范围内的修改不计,现将随1704全图底本绘出而《四十景》尚未呈现或是彻底改观的重要建筑、景区依年代次序列表〔表一〕,其中最后出现的景点、景观的建成时间,无疑最有助于判定图纸绘成的初始年代。
〔表一〕1704号全图绘出而《圆明园四十景图》未呈现或未改观的建筑
|
景点名称
|
添建或改建年代代
|
《圆明园四十景》旧称
|
|
藻园
|
乾隆十七年(1752)
|
未收入《四十景》
|
|
廓然大公八景
|
乾隆十九年(1754)
|
廓然大公
|
|
春雨轩
|
乾隆二十年(1755)
|
杏花春馆
|
|
君子轩-藏密楼
|
乾隆二十三年(1758)
|
属福海北岸涵虚朗鉴
|
|
多稼轩十景
|
乾隆二十四年(1759)
|
映水兰香
|
|
紫碧山房
|
乾隆二十五年(1760)
|
未收入《四十景》
|
|
竹密山斋
|
乾隆二十七年(1762)
|
别有洞天东山坳添建的园中园
|
|
澄练楼、开鉴堂
|
乾隆二十八年(1763)
|
接秀山房
|
|
安澜园
|
乾隆二十八年(1763)
|
四宜书屋
|
|
若帆之阁
|
乾隆二十九年(1764)
|
未收入《四十景》
|
|
清旷楼、华照楼
|
乾隆三十一年(1766)
|
方壶胜境北部天宇空明
|
|
汇万总春之庙
|
乾隆三十四年(1769)
|
濂溪乐处南部
|
|
文源阁
|
乾隆四十年(1775)
|
水木明瑟北部原四达亭
|
|
法源楼
|
乾隆四十四年(1779)
|
月地云居东部点景农舍
|
如上表所示,十四处有确切纪年可征的著名景观,最晚出现的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为筹备迎接六世班禅进京祝寿而在藏传佛教寺庙月地云居东部新建成的法源楼[5],据此认定, 图纸的绘成年代不应晚于是年。
乾隆四十四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标志。此后图纸中陆续出现的百余处粘贴修改方案分属乾隆、嘉庆、道光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就中最关键的仍然是乾隆朝的图像变化。与上述鉴定方法相逆,改绘、粘贴越早的景点、景区,其时间上限就越接近图纸绘成的年代。限于篇幅,仅将图中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后出现的重要改建项目择要列表如下〔表二〕:
〔表二〕全图中乾隆四十四年后出现改动的重要建筑项目
|
景点名称
|
建造年代
|
《圆明园四十景》旧称
|
|
兰亭八柱
|
乾隆四十四年(1779)
|
原坐石临流兰亭
|
|
知过堂
|
乾隆四十七年(1782)
|
原濂溪乐处云香清胜殿
|
|
宝莲航
|
乾隆四十九年(1784)
|
濂溪乐处水中石舫
|
|
秀清村六景
|
嘉庆十四年(1809)
|
别有洞天
|
|
恒春堂、戏台
|
嘉庆十六年(1811)
|
武陵春色
|
|
镜远洲
|
嘉庆十六年(1811)
|
平湖秋月
|
|
课农轩
|
嘉庆二十一年(1816)
|
原北远山村皆春阁群楼
|
|
观澜堂
|
嘉庆二十四年(1819)
|
接秀山房
|
|
涵月楼
|
道光七年(1827)
|
上下天光
|
|
慎德堂
|
道光十一年(1831)
|
九州清晏原乐安和寝宫区
|
无独有偶,最初呈现变异的坐石临流景区[6],档案中记载的竣工时间恰也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与法源楼的建成年代适相重合。
两处景点,一随原图一次性绘就,一在绘成后贴纸修改,时间都锁定于同一年,由此最终判定故宫1704圆明园全图的绘制时间为乾隆四十四年〔图二:1、2 〕。
〔图二:1 〕1704年底图上的坐石临流原图 〔图二:2 〕乾隆四十四年坐石流临修改粘贴图
1704号全图成图以后,陆续记录了自乾隆四十四年至道光十一年这52年间圆明园中的一切重大变革。图中最后一次重要修改记录是道光十一年(1831)建成的慎德堂,厥后涂改痕迹戛然而止。而就此定格于道光十一年的圆明园本部平面图像则成为众多尚无确切纪年的圆明园图档的重要参照物。以本年为界定的时空分野,厘清了某些图纸、甚至是改建工程的基本年限。
比如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排架第34包7号碧澜亭图纸,与1704号图中的若帆之阁西部平面殊相一致[7],实乃若帆之阁残本。今以国图多幅若帆之阁的细部平面以及故宫图书馆其他圆明园全图(某些仅勾画景区轮廓的旧图不计)中显现的该景区结构与前二者比较,则无一雷同;由此判定这些图纸的绘制时间皆应晚于道光十一年,而若帆之阁的改建当然亦在此年以后。
再如,1704号原图中,杏花春馆西院杏花村三卷房与国图样式雷91包1号图所显现的曲尺形平面结构趋同,知后者绘于道光十一年以前。反之,国图诸杏花春馆分景图中,杏花村三卷房均呈现规整的改建后格局,自然应属于此年以后的地盘图。依此类推,1704号图中长春仙馆的平面情况与《四十景》基本吻合,西院中戏台、扮戏房仍存,为目前所见本景最早图档。而国图样式雷第16包长春仙馆全图中的戏台均已无存,证明此包大都为道光十一年以后的改建图纸。
故宫1704号全图中,东止前垂天贶水门、西经长春仙馆西部土山直抵圆明园南大墙,环绕后湖九岛的东、北、西三面绘有一圈红线,水口处并有五处水关图示,显系后代添加,以后又被白粉涂盖,为众多圆明园全图中所仅见。红线极有可能表示围墙,连同水关,将后湖九岛封闭。是实际存在过的工程,还是仅限于拟建方案?如果确曾存在,那么建于何时?因何而建?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8]。
三 作者研究
乾隆四十四年,正是著名的样式雷家族第三代传人——雷声澂(1729-1792)执掌清宫样房楠木作事务之时[9]。
雷声澂不是雷氏家族声闻最显赫的设计师,但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生于雍正七年,为雷金玉幼子,尚在襁褓中雷金玉即辞世,由寡母张氏一手养育成人。
众所周知,圆明园的设计始于雍邸而完成于雍正年间,种种迹象均表明雷金玉是参与奠定圆明园主体结构的重要设计者之一。这从雍正年间雷金玉供役圆明园样式房楠木作,殁于掌案之任,始终得到皇帝信任的情况可见一斑。但自雍正七年雷金玉过世后,直至雷声澂重回样式房,二十年间,皇家工程设计另有其人[10],雷家在清宫样式房的地位一时间出现了断层。
雷声澂幼年失怙,母亲张氏呵护鞭策,矢志不渝,至于成立。声澂曾就读国子监,为太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正合小木作包含范围极广、需要多方面造诣和才能的条件[11]。乾隆朝人才辈出,在没有直系父辈提携的情况下,雷声澂开始只能是作为样式房的一般技师,辛勤劳作。他最终凭借自身实力争回楠木作掌案一职并监理样式房,成为皇家总设计师,其间所经历的困苦艰辛非一般人可以想见。无雷声澂,则雷氏父祖两代大匠之声闻、衣钵无以传,厥后家玮、家玺、家瑞三兄弟的事业根基无以立,更不会有景修、思起、廷昌后代儿孙的辉煌。雷家得以世守祖业,最后垄断样式房,特赖雷声澂筚路蓝缕,承先启后,克绍家学。声澂与三子生逢乾隆盛世,见闻经历亦非后世子孙可比及。如果说雷金玉之于圆明园的设计乃是缘于七十整寿之时雍正皇帝特命皇子书“古稀”匾以赐,以及殁后赏赐“百金”等荣耀的合理推论,那么雷声澂父子之于乾隆朝圆明园的一系列改建工程的设计参与则是实实在、有图可征的了。
从1704号全图中不见任何建筑景名、题额及文字注释的情况来看,知是雷氏留作自用的标准样底。图中的几处字迹笔力孱弱,不似曾为太学生之人的手笔,或为家玮、家玺、家瑞三人中某位少年时代的手迹?
乾隆朝的改建工程,四十四年(1779)以后见于图中的依次有坐石临流“兰亭八柱”、濂溪乐处“知过堂”和“宝莲航”石舫。即使不能完全认定以上三处就是雷声澂的设计,但声徵参与其事应无疑议。正因此,这一幅极有可能由他亲手绘制的圆明园全图才愈发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而弥足珍视。
雷声澂卒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离京承办皇差的任上,可谓是鞠躬尽瘁。声徵去世时,长子家玮、次子家玺、幼子家瑞均已在样房当差行走有年[12]。特别是次子雷家玺,自乾隆末至道光初,曾担纲承办乾隆万寿点景、三山、避暑山庄以及嘉庆帝昌陵等重要工程,御园圆明园自不待言。家瑞亦曾代其兄料理样式房,则此图中的修改设计方案出于家玺、家玮、家瑞兄弟之手殆无疑问。
雷家玺一生勤谨,道光五年(1825)临终时,虑及二十三岁的儿子雷景修虽然已有数年样房操作经验,但毕竟年轻,而皇家“差务慎重唯恐办理失当”,故将掌案一职让给了同辈郭九。仅此亦足见当时样式房中的设计人才并不限于雷氏一族。雷景修最后争回掌案一职已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事,从此直至清亡,这一重要职位均由雷氏后裔担任。
道光朝内忧外患,除皇陵大工,皇家园林基本陷于停滞状态,盛况难再。雷景修在协助他人承办差务之时,开始系统整理祖传档案图纸。故宫1704号全图中的修改痕迹在道光十一年(1831)以后突然中止,究其原因,很可能是雷景修注意到这一祖传图本的珍贵性,庋存收藏,不再使用。
今天能够推知出于雷声徵手绘、又经由雷氏家族三代设计师使用的圆明园图纸仅此一件,其上前后添加、涂改处历历可辨、渊源有自,时间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说它凝聚了雷氏一门哲匠的心血结晶,诚非过誉。
四 史迹钩沉
从康熙末年雍邸赐园初创到乾隆四十四年的天朝第一园,70年的缔构经营,圆明园已成为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重山复水、殿阁亭台合成的园林整体,表达并隐喻了园主人对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以及道德秩序的最高境界的理解和企盼。
作为清代皇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圆明园本部在雍正末年即已定型。乾隆朝国力臻于极盛,皇家园林建设达到巅峰,对圆明园的踵事增华几乎无日无之,此后历代君主也都依照自己的意志损益增减,某些著名景点或变异特甚,或面目全非,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
1704号圆明园全图是目前所知绘制年代最早的圆明园图纸,一些屡经改易或是久已湮没无存的景点平面在底图中奇迹般地得以保存[13],连同粘贴的修改方案反映出同一座园林以及园中同一景点在不同时期的变异发展情况。而对全图中蕴藏的久已阙载的景观进行发掘整理,有助于全方位把握了解圆明园的历史,特别是各个时期独有的理景手法和风格流变,钩深致远、探幽发微,其珍贵性是任何语言文字都无以替代的。
因篇幅所限,仅略举数例,尝鼎一脔,百年沧桑蜕变,尽萃集于这一张旧图之中。
1.上下天光
后湖九岛是圆明园的历史核心,也是圆明园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心景观。一如雍正朝官窑和宫廷艺术品的精细无疵,九州的总体结构疏密有致,风物尽态极妍,在建筑造型、山水结构、植物配置等多方面均已形成难以逾越的高峰。它们既不同于畅春园、避暑山庄的简洁大度,也不同于长春园、清漪园的巨丽恢宏,其精微缜密,秾纤适中,自成一种雍容而不失秀逸、浑厚之中又温文娴雅的雍正风格。
1704号全图所表现的后湖九岛,与乾隆九年的《四十景》相较,一半以上都已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上下天光和杏花春馆。杏花春馆尚有数幅分景图纸可寻,而乾隆中期完整的上下天光平面则为仅见〔图三:1、2 〕。
上下天光建成于雍正初年[14]。从《四十景》看,主体建筑半入湖水之中,非轩非榭,亦楼亦亭,云台风观,大有凌空欲飞之势,是后湖建筑造型最为奇绝的亮点。一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室内设楼梯通往二层平座之上的三间卷棚式歇山敞宇。左右虹桥卧波,蜿蜒动影,桥中段点衬造型各异的亭榭,有意打破对称,与今日遗址呈现的最终形局相去甚远。
全图显示出的乾隆四十四年“上下天光”平面介乎于乾隆九年《四十景》和遗址现状之间,主楼形式未变,但东、西已改建为对称的六角亭,曲桥规模也明显缩减,适与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日下旧闻考》中的相关记述吻合[15]。乾隆朝的上下天光图纸仅国家图书馆样式雷排架43包1号略显曲桥轮廓,对比研究,不仅弥补了文字记述以外的图像空白,更重要的是它映现出自雍正原创追求飘逸出尘的境界,到乾隆中晚期日渐讲求皇家对称均衡的形式,直至后期全面改观,将造型奇绝、仿佛天然出自于水中的镜面楼台变为俯瞰沧波的临湖宫殿——这一建筑逐渐脱离经始意匠的变化过程,实际也正是圆明园总体风格逐渐变异发展并日趋宫殿化的历史进程。
〔图三:1〕乾隆四十四年上下天光平面
〔图三:2〕乾隆九年《圆明园四十景》上下天光
2.武陵春色
雍正时代的圆明园,除九州、福海以及开旷的田园风光之外,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半封闭式的山水、庭园空间,亦即自成一体的园中园。虽然山水建筑的整体气势较康、乾两朝逊色,但结构往复回环、奇正相生,特重建筑单体造型的奇异新巧,群体组合的错落变化,山水画面的清新完美,文化意蕴的深沉隽永,其精雕细琢为二者所不能及。
武陵春色雍邸时称桃花坞,是雍正风格最杰出的代表。此处不仅是“桃花源”的再现,也是与桃花主题相关联的仙话的整合。桃花,伴随着山水的开阖延展,成为促成环境因素情感化上升的园林主题;而作为景观主体的自然风光,无疑包含了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憧憬的世外桃源和南朝刘义庆《幽明录》所记载的汉末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双重隐喻。
表现在景观结构上,设计者安排了水陆两条游览线,一缘溪,一循谷,仙源的意境随空间环境的变化而展现,随季相交替及游人心境的不同而移易;说此地是桃花源可,说此地是刘晨、阮肇遇仙的仙家洞天亦可。
1704全图显现的武陵春色平面与雍邸“桃花坞”诗及《四十景》图大异,全璧堂围房几乎将所有的山林空地占满,规模之大远远超出景观主题所能负载的范畴,与桃花源的境象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图四〕。
据《清昇平署志略》一书记载,嘉庆初年,武陵春色曾住南府“内大学”[16],山环中的围房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功能方面的需求所致。联系嘉庆十七年(1812)在此建成恒春堂戏台的史实,则全璧堂大型围房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雍正朝刻意经营的山坞空间——处于景观中心的一区仿佛与世隔绝的山野原田——成为清宫御用戏班班底“宿舍”所在地,此地与外界分离,隔音且便于管理,实际已成为御园中一处重要的演剧和排练场所。
〔图四〕武陵春色

1704号图中的细节回应了文献记载,钩沉出武陵春色一景在乾、嘉年间鲜为人知的根本性变异:雍正年间的双重游览路线仅有水路仍存,山林田园不复可寻,代之以集宴乐、游赏于一炉的世俗建筑群,清歌曼舞,锣鼓声喧,桃花源的整体意境已非全壁,那种移行其间,在时空转换中获得的完美空间体验和视觉感受也随之消失了。
3.接秀山房——观澜堂
接秀山房位于福海东南岸,雍正九年(1731)初成,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乾隆二十八年(1763)局部改建,因原型被观澜堂取代,兼以图纸无存,具体情况一直是悬而未决的疑案。
1704号全图保存的原稿使乾隆改建之后的接秀山房重见天日,也意外澄清了本景写仿江南原型——扬州九峰的历史事实〔图五:1、2〕。
就接秀山房、开鉴堂一组建筑的平面结构看,建筑多为三间或两间,小巧玲珑。开鉴堂造型复杂,显然属于非标准化的构造做法。相对于日趋定型化、模式化的御园官式建筑而言仿佛注入了一息新鲜活力。
偶阅清宫造办处档案,有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如意馆一条,其中“接秀山房澄练楼楼下……北间北墙着姚文瀚、陆遵书画《九峰园图》绢画一幅”[17]一段文字十分引人注目。
按,九峰园为扬州名园,一名砚池染翰,安徽歙县盐商汪氏别墅。因地处城南,俗称南园。据清人沈复《浮生六记》:“九峰园另在南门幽静处,别饶天趣,余以为诸园之冠。”乾隆壬午(1762)弘历第三次南巡,作《题九峰园》诗,次年五月,御园澄练楼一区即告落成。
接秀山房澄练楼一区与扬州九峰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将1704号底图与清代九峰园写景图对看,不难发现接秀山房、澄练楼一区以及开鉴堂的平面结构与扬州九峰园的吻合之处〔图五:3、4〕。但因地域有限,九峰园被灵活变通为澄练楼与开鉴堂两部分,撮其要、取其精,因地制宜:澄练楼有似御书楼,开鉴堂则颇具九峰园中“一片南湖”玻璃厅的场所精神。相对于扬州九峰园,朝向、转折虽有变异,但总体不谬。开鉴堂——澄空宇,连命意也颇相近似。
〔图五:1〕接秀山房——澄练楼原图(乾隆二十八年)〔图五:2〕观澜堂粘贴图层(嘉庆二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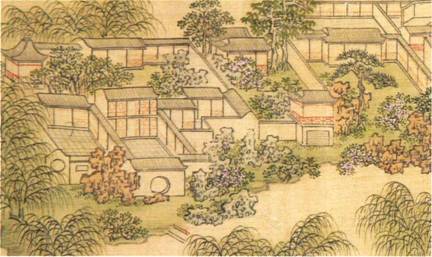
〔图五:3〕清人九峰园写景图(局部)
澄练楼中姚文瀚、陆遵书合笔的《九峰园图》无疑具有纪念意义,它不仅是皇帝南巡的纪游图,也成为眼前实景与江南印象之间互动的媒介。接秀山房的形势恰似南园临阔水,面沧洲,兼以西山叠嶂“朝岚霏青,返照添紫”,较原型更胜一筹。可以认定,接秀山房澄练楼、开鉴堂一组建筑正是扬州九峰园的变体。
接秀山房、开鉴堂的原始平面揭示出乾隆朝圆明园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相对于原创性极强的雍正朝景观,只能是见缝插针,修修补补,且处处要顾及、考虑到既成格局。九峰园的仿建对福海景区几乎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影响,一如方壶胜境人工盛饰的仙山楼阁,安佑宫、清净地等庄严庙宇的对称性铺陈,境象虽迥异于雍正朝的精微细腻,但其外部空间构成仍然基本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平地造园尺度控制原则。也正是囿于这一局限,自乾隆八年起,弘历将皇家园林建设的重点由大型平地园转向大规模天然山水风景区的建设。可以说,完成于乾隆九年的《四十景》实际是雍正风格的集大成表现,乾隆风格的最终实现不在圆明园,而是此后的长春园、清漪园。
嘉庆二十四年(1819),原接秀山房写仿扬州九峰园的一区精巧庭园被综括为观澜堂三卷大殿,由此形成了福海东岸皇帝游赏、起居乃至节日庆典(端午节赛龙舟、中元节放河灯)的重心所在。
以观澜堂为代表的外观造型厚重、而内部空间结构极尽丰富变化的连卷式大殿无疑是对乾隆中后期写仿江南的小型园林日渐琐碎、求多求全的建筑风格的某种反动〔图五:5〕。
〔图五:4 〕乾隆九年《圆明园四十景》接秀山房 〔图五:5 〕观澜堂遗址
观澜堂西临福海,遥望蓬岛瑶台,高堂深殿,面阔五间、进深六间、周围廊,五六三十,合于天地之“中数”——一如嘉庆《绮春园三十景》的象数学定位,反映出嘉庆皇帝在“形而上”层次对于宫殿建筑的理解和对复合式大型起居、游赏空间的钟爱。嘉庆、道光两朝,以追求丰富的视觉感受和空间体验为主要目的的园林景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园林建设日益表现出功能主义的倾向,许多规仿江南名胜的建筑群组被拆除,别有洞天、平湖秋月、课农轩的演变历程无不是将数处小型点景建筑综括为单体量的大型起居空间。观澜堂最终成为道光朝九州清晏皇帝寝宫慎德堂的母本,正是这一注重起居安适的创作主流的最终实现。
五 结语
圆明园在经历了钟鸣鼎沸的繁华之后,悲剧性地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烈劫火中化为一片焦土,曾经的地上繁华已永远成为记忆中的陈迹,而遗址又日益被城市现代化的躁动和喧嚣吞噬,逐渐变质。面对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这一张旧图,我们无异于面对历史:全盛时期万园之园的一幕幕次第展现,十八世纪中华帝国曾经的辉煌赖以留存,蕴含其中的民族文化精粹得以蔓衍,一部样式雷家族的设计史呼之欲出……
故宫博物院1704号圆明园地盘图是目前所见清宫样房圆明园图纸中绘制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表现内容最丰富、记录变化最全面的一张标准全图,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与1704圆明园图命运相伯仲的档案图纸:它经由雷氏家族世代相传,全面记录了乾隆四十四年圆明园的原貌和此后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流变,跨越三朝,几乎囊括了一部乾嘉全盛时期圆明园的变迁史。乾隆朝的旧图从来屈指可数,而一幅完整的圆明园全图就更是了如星凤,其重要性必将随着圆明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遗址保护利用的科学规划而愈益显现。
1779年至今,已整整二百三十春秋。二百三十年间,故宫1704全图经历了圆明园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进程,它记录了自乾隆四十四(1779)年至道光十一年(1831)圆明园中的一切重大变革,侥幸逃过庚申劫难,因雷氏家族的败落辗转流入中法大学,最后回到故宫,在图书馆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终于重现人间。
[1]端木泓,旅法学者。该文原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1期,经作者同意,本期《圆明园研究》转印此文,在此向端木泓先生致谢。
[2]该图仅后湖周环“苏堤春晓”“四围佳丽”“鸣玉溪”三处有侧欹潦草的楷书景名。
[3]这是唯一近真并能够在其他图纸上得到印证的数据。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排架98包3号图中标注:北面大墙长528丈9尺;另据1965年实测,圆明园北苑墙总长1694.5米,误差不大。图中安佑宫左近西园墙处标有258丈、32丈5尺等数据,连同后湖等处标注的一应数据尺寸尚有待甄别厘清具体所指。
[4]以圆明园为例,已经定型或少有改变的著名景观如镂月开云、天然图画、舍卫城等十余处,其分景图纸百寻不得一见。而九州清晏因是清帝寝宫,历朝添加、改易不断,存图竟达数百件之夥。
[5]少许白粉涂盖处仅限于对土山和围墙无伤全局的修改。图中绝无粘贴痕迹。
[6]坐石临流,《圆明园四十景》之一,雍正初年已建成。乾隆四十三年钩摹《兰亭八柱帖》,将重檐四方亭易以石柱,改建为重檐八方亭。这在四十三年夏,皇帝所作《夏日养心殿》“……薰风来殿阁,亦自生微凉。近正抚兰亭,即景玩词芳”的诗句中亦有体现。按,摹刻、改建工程至少需一年以上,兰亭完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当无疑问。
[7]与此图相对照,图中字迹与“四围佳丽”、“鸣玉溪”笔体绝似,墨彩渲染也表现出相类似的时代特点。
[8]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曾经谈到,2007年九州景区植树时,曾在茹古涵今隔水西岸土山西北角挖出过砖石基址的遗迹,为传统的灰砖并白灰粘合,周围均是山坡,北边为土山,南面已到了尽头,是否就是图中红线所示意的墙垣、水关遗迹?
[9]样式雷家族是有清二百多年间主持皇家工程设计的重要建筑世家,祖籍江西,自第一代雷发达进京,至清亡,前后八代。楠木作,即《营造法式》中的小木做,属内檐装修范畴。
[10]推测雷声澂重新回到样式房的年龄或在二十岁左右,即乾隆十五年前后,且一开始也不可能担当重要职务,只能是从头做起。雷氏家族的重新显赫应该是雷声澂执掌清宫样式房楠木作事务之后。
[11]见《精选择善而从》。直到晚清,雷氏一门最为拿手的还是硬木装修,亦即内檐装修设计。雷思起曾一再提到这是雷家的祖业。当然,大木对于雷氏也绝非陌生。
[12]雷家玮(1758-1845),雷声澂长子,生于乾隆二十三年,嗣业样式房。曾查办外省行宫,道光二十五年卒。雷家玺(1764-1825),声澂二子,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在雷氏三兄弟中最为出色。雷声澂殁后,先后担纲承办一系列皇家重要工程。因劳心过度,于道光五年最先去世。雷家瑞(1770-1830),生于乾隆三十五年,曾掌案南苑大修工程。道光十年卒。
[13]如武陵春色全璧堂在图中的结构为目前仅见,接秀山房、北远山村的原始结构得以复原,舍卫城绕城一周林立的商街,其规模之大,已远远超出今人可能想象的范围。紧邻城脚下的花街店铺,窄小玲珑,它与舍卫城前仿佛是京城商业通衢的买卖街对应,成为另一类型的江南商铺的集萃。
[14]《日下旧闻考》卷八○“国朝苑囿”:“……上下天光,左右各有六方亭,后为平安院。”上下天光改建前后的空间结构各具特色,但若就园林艺术的新奇丰富而言,雍正原创无疑更显匠心,建筑与山水树石的穿插进退、比例推敲、内容裁剪、均恰到好处,就后湖总体风格而论也更趋完美一致。
[15]乾隆朝上下天光改建于何时?档案阙载。杏花春馆的雍正朝村舍仙居在乾隆二十年(1755)大规模改造,变态为宫廷风格的山水园。不仅是空间结构,连岛屿形态也发生了变异。圆明园日益向规整化、对称化的程式套路迈进。即如“坦坦荡荡”添建鱼池,东面添建方亭,讲求对称,其北添建华贵的碧澜桥。上下天光“蜿蜒百尺”的虹桥有无可能在此时被改建成为规范对称的东西六方亭及曲桥?在综合权衡后湖整体景观效果之外,或许还有着便捷清帝水上交通游览路线的功能考虑?
[16]《清异平署志略》道光元年四月二日总管禄喜摺。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活计档(如意馆3524)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第17期,转发请联系原作者。
|

.jpg)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