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24日9:00-11:30(北京时间),“资本主义与环境”线上圆桌会议上午场在Zoom会议平台上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办。上午圆桌会议的与谈人包括:凯特·布朗(Kate Brown, 麻省理工学院)、亚当·罗姆(Adam Rome,布法罗大学)、克里斯汀·罗森(Christine Rosen,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马克·斯托尔(Mark Stoll,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堪萨斯大学)等五位学者。14:00-17:00(北京时间),“资本主义与环境”线上圆桌会议下午场在腾讯会议平台上举行,与会学者在回应上午场讨论的同时,探讨了他们对会议主题的思考和理解。本场圆桌会议的与谈人有(按姓氏拼音首字母先后顺序):付成双(南开大学)、 李伯重(北京大学)、梅雪芹(清华大学)、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与谢湜(中山大学)等老师。两场圆桌会议的主持人均为中国人民大学侯深。会议采取圆桌讨论形式,上午场的讨论以英文进行,下午场以中文进行。
整场会议向各种视角开放,涵盖的议题包括绿色能源革新、人类工作环境的健康、大众消费的力量等。部分讨论以资本主义为透镜审视自然,部分讨论则思考其与传统的,或者社会主义的文化、经济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冲突和共同点。会议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与19世纪的工业化相比,现代的环境历史是否能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提供一种更为成熟的阐述?伴随时间的推进,资本主义的观念与实践是如何演化的?环境差异究竟在何等程度上形塑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全场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每位与谈人介绍其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其次,各位与谈人之间进行讨论讨论;随后,听众提问环节;最后,与谈人简短地总结发言。
我们考虑过各种呈现此次会议的方式,最终决定,由于发言人的讨论精彩纷呈,因此生态史研究中心同仁通过录音整理,尽量重现当时会议场景,拟将之分作六次分别报道,以飨读者。会议分记录整理人包括(按姓氏拼音首字母先后顺序):曹芷馨、陈双志、方文正、葛蔚蓝、蓝大千、李彦铭、刘叶、孙一洋、吴羚靖、肖苡。汇总人:郑坤艳。
上午场 Part 01 个人发言

凯特·布朗(Kate Brown)
凯特·布朗:唐纳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问题,我将会告诉你们我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并将其同我在过去的研究相联系。
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在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如果从人新世(Anthropocene)的角度出发思考,资本主义是人类所有意识形态创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自近代早期到2021年,市场扩张对环境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见到1950年后一系列有毒与有害物质,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高速增加,彼时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已经像蛛网一样扩张到全球;至少就其在环境层面的表现而言,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并未带来很大改变。就我所熟知的苏联的情况而言,我会将他们所实行的苏联体制称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因为资本主义霸权设下发展的标准,该标准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成功的度量衡,社会主义势力不得不全力与其对手竞争。通过定义良好生活所需的空间大小、拥有汽车数量、摄入的卡路里,美国人提升了人类生活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下,消费水平成了人们评判社会与自我情况的标准。
这里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依资本主义国家方式行事的例子。两天之后,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三十五周年纪念日了。当这起悲惨的事件发生时,该核电站正在开展一项增加核电站运行效率的试验,尝试让旋转的汽轮机在反应堆与发电机均关闭之时仍尽可能地产生电力。如果试验成功,则电站可以产生更多额外的能源。电站中的操作员与经理均可从中获益,因为同他们在美国核电站中的同僚一样,他们电站的发电量越多,月薪中的奖金也就越多。发生了爆炸的是著名的四号反应堆,但最常为我们见到的可怖场面之一发生在它隔壁的三号反应堆之上。年轻的士兵们冲上三号反应堆的屋顶,奋不顾身地将灼热、危险、带有辐射的灼热石墨从屋顶上铲走,他们并非为了终结这场事故,而是为了让三号反应堆尽快恢复正常运作。成千上万年轻人被暴露于辐射中,仅为产生更多电力,赚取更多财富。我想此间逻辑任何生活于美国之人都应深感熟悉。
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围绕稀缺资源展开的竞争,劲敌间优胜劣汰的冲突,成功进入了所有形式的知识之中,其中尤以与环境史联系紧密的科学与生态学受影响最深。今日我们已深知此逻辑之荒悖。组成森林之树木在彼此间分享营养与毒物的存在、枯萎病来袭的消息。一株濒死的树木会将自身资源让给附近的树,完成一种跨物种的利他行为。换言之,这些林木在互相合作中塑造了一个互帮互助的社群。在本地生活的居民对此一清二楚,并曾声称事情本应如此。西方科学偏离了曾经普遍存在的、对自然生态系统成员互帮互助的知识,而引入了彼此猜疑畏惧、无休无止的竞争与适者生存等关于资本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竞争,其中尤以军事为最。社会主义国家认定,只有不断生产武器,才能赶上资本主义国家,以保护自身疆域。他们不断生产各种传统的、化学的、运用核能的武器,维持一只规模庞大的军队,参与或大或小的战事,付出巨大代价。
在资源的层面上,我自己的研究可以提供重要例证。在就美国与苏联的钚(一种用于核武器中心的元素)生产展开研究,写作《钚托邦》(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一书时,我惊讶的发现各国的核设施会向周边环境中排放越3.5亿居里的核废料——让我大感震惊之处不在于核废料之多,而在于美苏两国的数字竟然如此相似。苏联与美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与国家文化均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却生产着同样数量的钚与带有辐射的废料。我发现,这并非出于偶然。在两国中生产钚的人们达成了一种无须言明的默契。当美国人生产出反应堆,并在日本引爆了那两颗知名的核弹之后,苏联人立刻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反应堆,以作为对美国人的回应,打造自身的核屏障(nuclear shield)。当苏联人于1949年首次测试了他们的核武器之后,美国人立刻参与了这场军备竞赛,建造更多如汉福德(Hanford)区那样的反应堆,将其数量从五个提升到了九个。为图方便,美国人将产生的核肥料直接倒入河流、排入大气、埋入地下。通过对土地中核辐射的探测,苏联人发现了美国人的做法,并很快加以仿效。

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这也是我想要说明的最后一点。唐纳德问我们如何看待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定义,环境史学者是否仍应沿着他所提出的劳动与阶级关系、社会不公正与剥削的路径思考。我认为无需如此。在暮年,马克思对土壤科学产生了兴趣。他的一位同代人,查尔斯·达尔文也在暮年着迷于研究蚯蚓。两人都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土壤肥力耗竭话语的影响。时人认为,农人越来越难生产出与此前产量相同的作物,当然,唐纳德对此了解更深。马克思就此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的理论,指人们未能将营养物质还给它们来源的环境。关于马克思学术生涯晚期的生态学阶段,哲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之论述最丰。在他看来,马克思指出的土地与农业问题是现代“新陈代谢的断裂”,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断裂的起源。环境社会学家们今日称其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断裂(ecological rift of capitalism)。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的资新世(Capitalocene)概念是成立的。资本主义通过对市场及供给市场的原材料的追求,正在高速破坏着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这种力量实为此前人类历史中所未见。
剩下的发言时间不多,因此我将跳过一个问题,直接来到最后一个:我们今日实行的资本主义主要力量,是否可被利用来保护当下及未来之环境?我担心并非如此,而我们也将不得不转向新的模式。近来,我对城市食物自给的历史产生了兴趣。与之相关的历史似乎近在眼前,却为人忽视。在美国等许多国家,移民与来到城市的非裔族群在城市中自筑居所,并通过耕作获得自身所需的食物。1990年代,当我在苏乱解体后的俄罗斯时,该国农业崩溃,所有人都担心出现饥荒。但是预言中的饥荒并未出现。因为人们乘坐通勤火车前往城市边缘,种植足以自给的土豆。1996年,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使用国内1.5%的可耕地生产了91%的土豆。相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古巴及许多陷入困境的非洲城市中:人们利用土地种出自己需要的食物。我认为也许这意味着我们将关注类似的,我命名为“经济的原始化”的现象。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走向这条道路:回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互相合作的社会形态、重建公社及其他基于互助之上的社会。当我们这样做之后,我希望我们所处的环境会做出回应,这样我们或许可以从灭绝中拯救自己。谢谢。
(方文正翻译、整理)

亚当·罗姆(Adam Rome)
亚当·罗姆:过去30年间,许多美国企业开始思考可持续性以及如何更加环保的问题。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并未颁布可比肩于《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 1963)、《清洁水法案》(Clean Water Act 1972)或《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 1973)的新的环境立法。因此,企业无需做任何法律规定的事,企业所谈论的是超出合规性之外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企业愿意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走多远,又是什么驱使它们如此行事;更感兴趣的是,什么构成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障碍和限制。我认同沃斯特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是美国环境的驱动力和破坏力”,这也是美国环境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他认为企业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是也有例外之处。
通过我的个人经历,我想说明一下我对企业和环境问题的深入思考。10年前,我搬到特拉华大学,附近的哈格利博物馆与图书馆(Hagley Museum and Library)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企业史和技术史中心之一,这为我了解企业史提供了诸多便利。罗杰·霍洛维茨(Roger Horowitz)与我合办过一个国际会议,将企业史家和环境史家召集在一起,以探讨环境中的企业。最终,哈特穆特·伯格霍夫(Hartmut Berghoff)与我合编了一本源于此次会议的书(Green Capitalism?: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这次会议使我意识到企业和环境这个主题比我曾经想象的要丰富且复杂得多,而环境史家对企业的研究大都从企业外部的视角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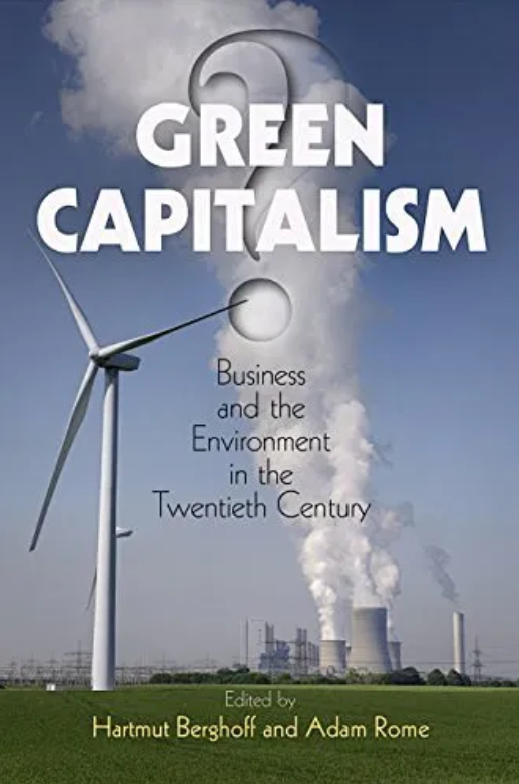
Green Capitalism?: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认为企业导致了所有的环境问题,而我所书写的那些人将企业视为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由此,我和伯格霍夫在编辑书的时候,分别从环境史的视角与企业史的视角写了两篇介绍性的文章。后来,我开始阅读大量有关企业和可持续性或环境中的企业的管理文献。但这些文献是约30年前的,其中一些其实可被视为同时代的原始档案,反映出人们在20世纪末是如何思考企业与环境问题的。这些文献讲述了商人的思考方式、决策方式和形成战略的方式。而我参与编辑的这本书使我意识到,企业与商学院教授们是在近30年里才开始认真思考企业与环境的问题。如前所述,我开始思考,在近30年间,企业与环境究竟改变了多少,又有多少没有改变。显而易见,对我们而言,可持续经济任重道远。但是,我做的初步工作也有助于提炼出一些问题,例如:我们的经济是否变得越发不可持续,或者,我们是否正在做一些为真正的绿色经济指明道路的事情?
我想解释一下造成环境问题的十大原因。我认为首要原因是美国人仅将自然视为财富的来源,而其他几个理由也基本与资本主义有关。首先,我讨论的是时尚问题,包括作为服装行业的时尚与改变生活风格的时尚。后者让人买更多的东西,扔掉那些原本非常有用的东西,而这已经成为消费者和消费经济的驱动力。我写了一篇关于时尚的评论,意识到目前有很多人追求一种他们称之为可持续时尚的东西。他们相信时尚是重要的,且其益处颇多,但他们也认为时尚是“破坏循环(cycle of destruction)”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认识到可持续时尚可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时尚通常意味着一些与可持续性直接相反的东西,二者很可能是不一致的。因为可持续性是关于持久性,而时尚是关于永无止境的变化。但这些人一直在认真思考这种很可能存在的矛盾是否能得到调和。当我再次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经济能否更环保的这个问题比我曾经想象的要有趣得多。所以,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准备探讨此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可持续性之路漫漫。因此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为何此路漫漫,为何企业活动是阻碍我们达到可持续性的巨大障碍。但我也认真对待许多公司的企业人士为了环境更好而做的事情,并试图了解他们的动机为何,以及动机不足在何处。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已经发表。
杜邦公司是一个相关的案例。我在特拉华州的时候,就和杜邦公司相邻。1989年,杜邦是第一个谈论超越合规性的公司,他们的一位CEO开启了企业环保主义(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的新时代。因此我写过一篇关于杜邦与企业环保主义的局限性的文章(注:“DuPont and the Limit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93, no. 1 (2019): 75-99.)。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了一些非常认真的改进,但是他们的记录仍然很糟糕,我想知道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思考企业为何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考虑超越合规性。原因有很多,但这些原因只是激励企业以一些方式超越合规性,而非以其它方式。并且,其中的一些原因也有点自我局限性。因此,这篇文章的最终论点是,即企业本身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内部理由以变得绿色环保,即使有可能实现绿色资本主义。虽然其可能性很低,但我们尚未付出很大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绿色资本主义的实现需要企业外部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将从根本上改变市场运作规则,并改变企业的本质。
最后,如果人们真的要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那么就必须思考什么是可持续经济,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在这方面有所帮助。
(葛蔚蓝翻译、整理)

克里斯汀·罗森 Christine Rosen
克里斯汀·罗森: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教授,在那里教企业史。我从1990年代开始教可持续企业,以及环境管理与战略的课程。我对企业感兴趣,但并非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讨论对我们对环境的剥削。我长期关注的是企业、企业管理者与企业领导者如何对待环境,尤其是污染和由工业引发的环境公害。正如罗姆所言,近年来企业管理者在减少环境破坏和碳足迹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在1990年代,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已汇集一整套与此相关的案例和文章,因为这个机构鼓励商学院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当时被这些公司的所作所为吸引,包括其面临的挑战,其如何制定策略以克服那些企业处理问题的既定方式,及其为此所使用的管理工具。
我有幸能够参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一个工程学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的项目(注:项目名为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erarchical Decision-Making in Life-Cycle Processing and Planning for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Products项目)中。该项目的首席专家(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涉足工业生态学领域,这是当时工程学中很有前景的领域。工程师开始思考如何设计并制造出能够降低环境危害的产品,工业生态学得名于此。当时我参加了一个由美国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主办的会议,众星云集,其中包括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学者与处于工业生态学研究前沿的学者。由此,我对工业生态学非常感兴趣。自那之后,我开始写一本与美国早期工业污染治理史的著作,目前接近完成。
资本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中扮演重要角色,且资本主义在人性、技术和国家等层面也很重要。从人类历史开始,人类就开始利用自然,并生活于自然中。我们的食物和燃料都来自自然。布朗谈到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合作,而我们利用自然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一种与自然合作的方式。驯化动物是一种对动物的剥削,但这同时也是动物主动靠近人类并允许它们自身被驯化,尽管有些动物不容易被驯化。

由此,我对这种关系很感兴趣,但我并不想谈论马克思所言及的对劳动与阶级等的剥削。我想从我的博士论文所关注的大火之后的企业领导力与城市重建的问题着手(注:博士论文题目为"Great Fires and the Problems and Processes of City Growth", completed in 1980)。我感兴趣的是企业领导者在改善与保护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领头作用,博士课题的研究时段是1840年代至1920年代。最初,我试图理解人们如何看待污染和环境公害。我研究了判例法的判决,或英式判决,其中大部分诉讼与污染问题有关,以试图理解美国人如何认知工业通过其工厂的排放等而导致的环境公害的新形式。当我看过很多诉讼案件后,我发现不仅他们所引据的教条因时而变,而且我所见与所写的法官与陪审团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案件事实,并将源于工厂的工业烟尘与废水视为问题,而人们有权利保护他们自身免受这些问题困扰的应有的法律行动。虽然某些污染在今日看来是很明显的环境问题,但是当时的法官与陪审团并未意识到这点。他们并未将烟囱里排放的烟尘当作有违法律的显而易见的污染问题。纺织工厂排放出的废弃物显然也是环境问题。然而,从内战开始,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大部分工业州的判例法有所改变,法官和陪审团开始将工业污染视为一个明显的环境问题,并且开始强加解决方案,向污染者征收损害赔偿金等。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以结构驱动的方式剥削自然和劳动力的体系,那么从这些资源中尽可能地获取最大的利润是该体系的内在特性。我最近的关注的问题是,当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其中的错误并开始采取相应法律措施时,他们会如何去处理这些环境问题?社会如何组织和开始重新规范或消除这些污染,保护人类远离这些排放物。我发现,在早些时候公共健康改革者很关心这类问题,他们试图有组织地调整并实施相关法规,但是他们没有权力。1880年代,在芝加哥、辛辛那提、匹兹堡和圣路易斯等一些美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中,进步的企业家通常与女权改革者和公共健康改革者合作,共同组织各种运动,以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不仅要让这些法规被通过,而且还雇佣他们自己的律师和工程师,来帮助那些有污染问题的企业符合合规性,并帮助城市官员起诉与惩罚那些违背合规的企业。
当我在思考资本主义是否可被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如何被用来保护环境这个问题时,我认同罗姆的说法,即我们可以参考那些进步且开明的企业领导者,以动员活动。我认为,目前企业内部的环保趋势有助于动员公众环境运动,以使环境法规变得更为严格,例如,使美国政府继续遵守《巴黎协定》。
就我自身研究和教学经验而言,我对资本主义抱以期待。资本主义不仅仅是邪恶与破坏性的可怕力量,其内部也有成为解决方案的能力,即通过企业领导者的行动及与剩下的其他人的合作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吴羚靖翻译、整理)

马克·斯托尔 Mark Stoll
马克·斯托尔:首先,我定义一下资本主义。我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表现为获利性质的贸易,即通过攫取自然资源或农业资源,发展工业或贸易,以实现财富积累。当这些积累的足够财富被用于贸易与生产时,就成为资本(capital)。
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中心定义来看,资本主义都依托于资本而存在。资本主义通过控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来进行贸易生产,这在历史上往往是强制、具有剥削性质的。并且,上述过程必须是廉价的: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庞大的体系必须要有大量的金钱,因此需要有廉价的能源、廉价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运输工具。若无上述廉价体系支撑,则资本主义休矣。
我关注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并将回溯其历史。以17世纪荷兰帝国的崛起为肇始,农业的商业化使纺织工业开始腾飞。随后,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建立,英国的农业商业化进程加快,纺织工业开始腾飞。到18世纪,英国飞速发展,丰饶的煤炭资源与先进的热科学(science of heat)使蒸汽机最终被发明,并由此引发了运输革命。铁路、运河和蒸汽船使得商品与原材料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运输变得十分廉价与便捷。而后在大量煤矿和铁矿的刺激下,钢铁工业得以大规模发展,到19世纪成为世界上领先的产业。煤炭中提炼的副产品煤焦油则使化学工业得以诞生。在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下,工厂往往集中分布于交通便捷且有廉价能源的地方,工人也集聚在一起,环境和卫生问题也随之而来。而从世界各处运输原料到英格兰也加剧了其环境影响。到19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最终从欧洲大陆扩散到美国、日本等地。
工业资本主义以生产为导向,力求便宜高效地生产商品。而到19世纪末市场已经饱和,此时问题便在于如何出售这些正在生产的商品。消费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由此产生,即通过各种创新方式刺激人们消费。与此同时,石油能源革命兴起,内燃机在20世纪得到广泛应用,这是另一种能源转型。在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渐趋成熟,迎来高潮,时为“喧嚣的20年代”。消费资本主义聚焦于让消费者更多地消费。分期付款与信用卡在20年代开始出现以刺激超前消费,当时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广告形式更加丰富,商品的更新换代也越发频繁,旧的产品未用多久便已被频出的新品淘汰。
消费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更是日臻极盛,影响范围也从美国扩展到欧洲大陆,到世纪末已蔓延全球。金钱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流动,以使消费资本主义得以运转;产量的提高,消耗了更多的能源和资源,也造成了更多的污染,并产生了更多的温室气体;增长的消费促使人们更快地丢弃旧产品;依靠化学品的农业企业也应运而生。在消费资本主义体系下,一旦消费停止,经济也会随之崩溃。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即为典例,然而人们并未吸取教训,到2008年又重蹈覆辙。
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尽管我们发展至今日,诸多国家已日渐繁荣,人类科技也在不断进步,目前已养活了数十亿人,且人们的寿命也在不断增长,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森林砍伐,物种灭绝、气候变化问题愈演愈烈,全球各地也存在着塑料和化学污染。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诸多跨国公司的兴起也使得利润在全球的分布愈发不均。
最后,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已久,然而它能够适应当前的环境吗?或许是可能的。在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趋势,即消费者不一定要购买生产出来的实体商品。而日渐兴起的电力经济(Electric economy)是一种潜在的可持续模式。人类有无数种方式来生产电力,当前也已有诸多电力列车、飞机和汽车被广泛应用。此外,当今世界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喜欢在他们的设备上进行电子体验,他们无需购买实物,完全沉浸于视频与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之中。我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认为在未来,人口增长压力将会减轻,从而减轻资源方面的压力。虽然人类深陷资本主义的泥潭之中,但也能够找寻到出路。
(蓝大千翻译、整理)

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唐纳德·沃斯特:我认为眼下这个时代是资本主义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代。新冠疫苗的发明、太阳能和风能、互联网通信等都表明资本主义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但其中很多问题其实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同时,鉴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目前也是一个有很多缺陷的时代。我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它有自己的历史、开端与终结。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在生产满足我们需要的足量的食物、医药与能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满足了人类对于生存和繁殖的最深刻的迫切需求。虽然资本主义从未承诺或产生绝对的公正,也从未承诺过“环境天堂(environmental paradise)”,但它确实承诺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上的成功,并将一直持续下去。
我理解的资本主义,首要的是一套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理念,即经济史家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Robert L. Heilbroner)所称的“世俗哲学”(worldly philosophy)。这些理念阐述了如何让我们与我们后代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全和繁荣。我认为,这套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将贪婪——也许是所有原罪(sin)中最致命的一种——转变为美德。简言之,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场道德革命。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受到市场刺激,以进行竞争性的买卖和分配,并且其也受到对自身利润的自由追求的影响。
我想特别谈论的是农业,因为农业位于道德知识革命(moral intellectual revolution)的最前线。如果你不能制造更多的食物,你将不会有机会在其他任何地方创造充裕(abundance)。在资本主义出现前,农业以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为开端,这意味着本质上要控制它们的繁殖。在99%以上的历史时间中,人类是作为采集者和狩猎者而存在,几乎没有控制过自然的再生产。但是伴随着这些对动植物的驯化,我们获得了控制再生产的权力,而非仅限于收获食物、纤维或能量。在接下来的1万年内,只有极小一部分人类控制的再生产在市场上售卖,几乎全部的产品都被那些靠土地生活的人消耗了。通过将农业分布于大多数人中间转变为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资本主义革命改变了上述情况。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与土地的疏离,或者你也可以把这当作将人类从承担提供自身食物、能量和药物资源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如今的农业领域里看到便是这样的现象。
我认为,农业资本主义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是人类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物种的繁殖。然而矛盾的是,地球上的动植物种类正在逐渐减少。一个需要提供所有家人所需食物的农民需要在同一块地上为水果、蔬菜、谷物和肉类去寻找空间。为此,农民必须减少野生动植物的自然数量,必须去破坏或缩减它们的栖息地,并将许多野生动植物从景观中抹去。但是,一个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耕农通常只销售谷物,并主要是供应城市和帝国。资本主义诞生后,专业化趋势随即出现,这保证了更高的产量和更优越的专业技能,给生产者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而且也正是这种专业化改变了土地的面貌,改变了这个星球上大部分地区的生态。农场变成了单一栽培。如果你进入了一个农民的厨房,你将会看到桌上摆着的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些食物可能来自于另一个省,甚至世界的另一边。正如斯托尔所说,运输这些食物需要相当多的能量。此外,运营那些处理食物的工厂或者将生长于世界另一边的种植园中的棉花加工为纺织品的工厂,也使所需的能量大大增加了。

肉眼可见的另一个改变是相对于私人企业的角色而言的不断变化的国家角色。早期国家从仅能维持生计的农民手中获取贡品。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开始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为灌溉提供用水,为消费者保证食物安全,管理国内和国际的贸易和货物,或者管理空气和水污染。与此同时,通过建立规模日益增大的组织以生产、加工和分配食物,新的资本主义者和农业巩固了其权力。这些物质上的改变正在欧洲和美国的农业历史中发生。
我认为,中国的故事与欧美是不同的。在所有政府都在尝试着去管理现代食物产业或者建立拥有和控制土地的秩序的时候,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将中国完全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之前,需要进行一些思考。在中国,那些能直接接触到土地并种植他们所需的食物的人的人口比例正在降低,一直以来,这个比例都在不同程度地降低。自从邓小平改革后,在中国的超市中,食物变得充裕而便宜。但是,在农场或食物加工设备方面,中国国有企业是否与由少数私人与股东所有的美国企业迥然不同?毕竟,这些企业都必须投入大量的金钱,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变为更多的食物,以供养庞大的人口。
我从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得到了启发。给予农业的关注太少是他最大的缺陷之一,只有在他《资本论》的第一卷里有简单地提到,而那写于19世纪60年代,并且正如布朗已经提及的那样,其主要谈论的也是“新陈代谢的断裂”。马克思死于1883年,恰好在资本主义的一个伟大胜利出现前,即现代化肥工业的诞生。通过学习如何将关键的化学元素添加进土壤中,企业家们克服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将他们从土地中抢夺走的营养物质又还给了土地。由此,作物产量成功地在20世纪实现了飞速增长,中国也跟上了他们的步伐。而中国也开始制造自己的肥料,如今已经成为了这项资本主义发明的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也许,没有这些肥料,世界的一半人口将不会存在。
但是,如果恢复自然并不只是意味着将更多的化学元素归还给土壤的话,那该怎么做呢?如果需要保护整个动植物生态系统,那又该怎么做呢?马克思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资本家也没有思考过。我们要如何恢复和保护这颗星球整体的生态健康?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若马克思仍在世,他一定会严肃思考上述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一定会到来。同时,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几乎可以肯定,到本世纪中叶为止,世界人口将会增加30或40亿。
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资本主义在农业、医药或能源等方面的伟大成就,抑或是指出它的很多失败之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去跟随诸如亚当·斯密这样的哲学家,或者选择跟随卡尔·马克思?我们需要扩大我们想象力的边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我们的工作是,去引导其他的历史学家思考我们对地球已经做的以及正在做的事情的后果,思考我们如何改变了我们进食和消费的模式,以及最重要的是,思考这颗星球能安全供养多少人。
(刘叶翻译、整理)
|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