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愚蠢的智识一贯性是肤浅思想的小怪”,这是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一句名言,也是沃斯特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格言。我可以想见他在近60年前读到这句话时的震撼,彼时,他身处同样冰天雪地的新英格兰森林,困扰于自己离经叛道的博士论文选题为师长同侪的误解。不过,即使那时,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沃斯特或许也未能逆料,他在未来的智识之路上,将始终处于同那些小怪的战斗当中,我们眼前的这部书——《欲望行星》——正是他再次挑战自身智识一贯性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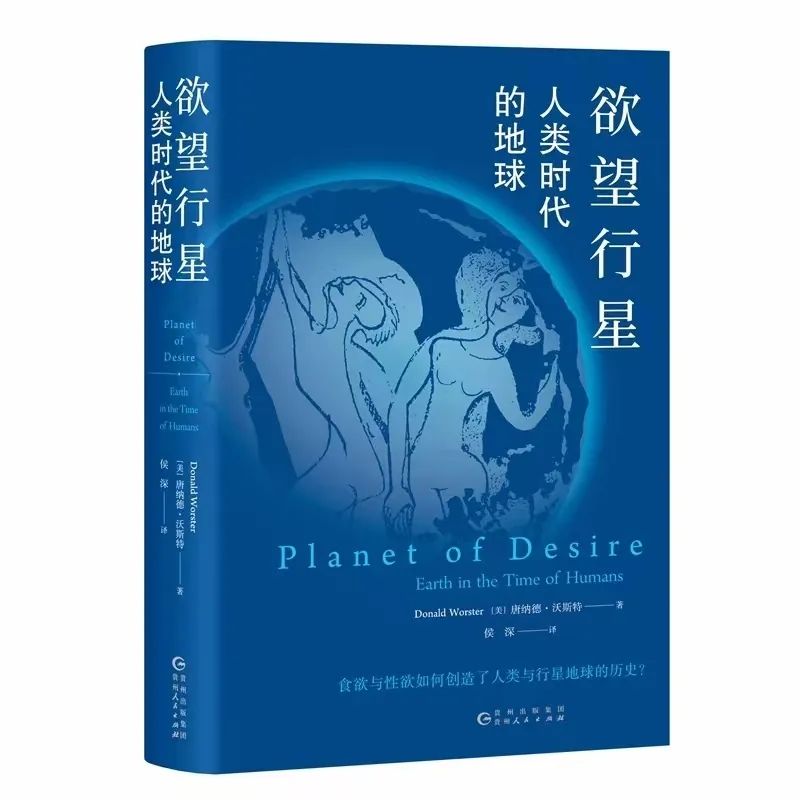
《欲望行星》书影
对爱默生而言,“愚蠢的智识一贯性”所指是对主流智识思潮的盲目追随。“自立”是爱默生思想的核心,它所要求的远不仅是个人与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自主,更是发源于自身直觉、仰赖自身的智识探索与分析而形成的独立思考。在其智识生涯的早期,沃斯特对抗的精怪更多是他身处的社会群体所遵循的主流。其中有他成长的大平原小镇,其社会文化沉浸于政治与生活意义上的爱默生式自立,但是在思想上循规蹈矩、信仰虔诚;也有他所求学的耶鲁大学,广厦林立,名师云集,但是刻板的传统与严格的规训鲜少留给学子思想野蛮生长的空间。当然还有他所生活的更为广阔的美国社会,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各色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年轻人经历着精神上的愤怒苦闷和行为上的离经叛道,但在他们身着奇装异服,吸食大麻鸦片,尾随人潮走上街头、涌入公社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新奇、叛逆、破坏的渴望,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挑战了他们自身一代的主流思潮?
显然,沃斯特属于那一小部分真正反思任何一层意义上的主流的思考者。他从未讳言那些以各种形式渗入其大脑皮层的习俗与思想对他的塑造,但是,他也从未让任何一种主义、信仰、训喻,或者惯性成为左右其思想的权威。当他的同学们或者循着导师的道路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诠释者,或者走出精英思想史的藩篱,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历程时,沃斯特决定走得更远,更深,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让历史学不再仅仅关乎人类事物,而令其融入远为浩瀚的自然演化当中,探讨人类与不为他们所创造的他者世界之间的关系。环境史因而诞生。
当然,在这条新的智识之路上,沃斯特并非孑然一身。但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这都不是一条醒目的康庄大道,标识清晰,目的明确,从游者众。反之,那几位最早的开拓者在一片尚未被标记的智识荒野中漫游,虽然不羁,但是孤独。对一个需要在竞争残酷的现代学术丛林中找寻安身立命之所在的青年学人而言,选择如此一条道路无疑是一场冒险。很多年后,当有人问及为何环境史率先出现在美国时,沃斯特回答道:“那时的我们很自由。”在这个层面上,他们无疑是幸运的,外部没有威权的高压,没有层层严苛、细碎的考核;内部没有大佬政治,没有等级体制。虽然大部分人仍然会选择一条宽广而明晰的道路行走,更早地找到更多的认同感;但是,彼时彼地的学术生态同样给了冒险者以生存的空间。
可能一个自由的灵魂永远是一个不愿安顿的灵魂。当环境史已不再是一个徘徊于历史学科版图之外的寂寞拓荒者,而在学术生态中找到自身恰如其分的生态位;当昔日的反叛者已成今日的权威时,那个反抗的幽灵再次浮现,而这一次被挑战的对象是其自身的智识一贯性。对绝大部分人,包括青年时雄心勃勃、誓不妥协的反主流者而言,古稀之年或在养鱼种花,颐养天年,或在收拾功业,志得意满,然而沃斯特开始了一场新的学术冒险,前往中国。

沃斯特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
在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生态史研究中心,沃斯特成为中心的名誉主任,同时受聘人大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开启了每年五个月的中国教学之旅。最初,同所有未曾真正认识这个国度,但是有着旺盛的智识好奇心的学者一样,沃斯特是以他者进入异域文化的身份执鞭中国。在他此前所有对中国的阅读中,贯穿始终的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异质性。正如在他所致力的美国史、西部史中,虽然美国例外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已然千疮百孔,但是对文化差异性的强调近乎成为人文学者的集体意识。所以,在他踏入中国时,他所寻找的是迥异于他所熟识的美国乃至西方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当他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离开中国时,他发现的却是驱动人类时代的行星演化的同一种巨大力量,所有生命共享的欲望。地球正是“欲望的家园行星”。
这并不意味着沃斯特试图抹杀文化之间、个体之间、物种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不意味着生命的核心欲望——食与色——亘古不变、寰宇皆同。事实上,地球本身的演化正是数以亿计的多样性之所以涌现、变化的原动力,从海洋到沙漠,从高山到平原,从雨林到极地,外在自然的存在如此千变万化,不同的自然系统孕育的生命形式如此五光十色,生命所蕴含的欲望,以及实现欲望的方式如何能够始终如一?欲望在演化,欲望在竞争,有些欲望被放大,有些欲望被压抑,在种种欲望的缠绕、竞驰中演绎着千差万别的人类故事。
但是,人文学者,包括曾经的沃斯特本人在内,太过关注差异,也太过关注思想的、道德的、文化的力量,而忽视或者回避人类共有的欲望对其自身历史以及行星历史的深层影响,罔顾智人物种在共同欲望的驱使下在这个欲望行星中不断扩张的生命之旅。当历史学者意识到每一个历史中的个体都应在历史学中享有平等的存在权利时,我们也不应无视所有人以及非人类物种共享着这个欲望行星中的过往。如沃斯特所言,这20万年的共有经历无法为一个简单的线性故事所捕捉,但是同样,它也不应成为一个个分裂的、碎片的国家、族群、个体故事的简单叠加。此前的沃斯特在时空的片段中,叩问改变人与外在自然关系的力量,如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现代性;而《欲望行星》中的沃斯特试图在作为巨大单一整体的行星地球中,找到人类之所以走入今天之境遇的本源驱动力。

沃斯特先生在俄勒冈州奥纳海滩(侯深 摄)
对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而言,离开智识生涯的旧径甚至可能比挑战主流思潮还要艰难,它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是如果一位学者仅仅沿着同样的道路踯躅流连,则他终将陷入肤浅思想的小怪的围攻之中,而终结自身的智识生涯。作为《欲望行星》的第一位读者和它的中文译者,我几乎可以预见在这个多元文化主义笼罩人文学界的时代中,此书将引起怎样的争议与批评,但是,同样如爱默生所言:“欲成就伟大,必先遭误解”(to be great is to be misunderstood)。作为终生拒绝“愚蠢的智识一贯性”的叛逆者,沃斯特想必早已对所有的误解做好了准备。
侯 深
于亚欧大陆上方1.2万米空中
编辑:蓝大千
|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