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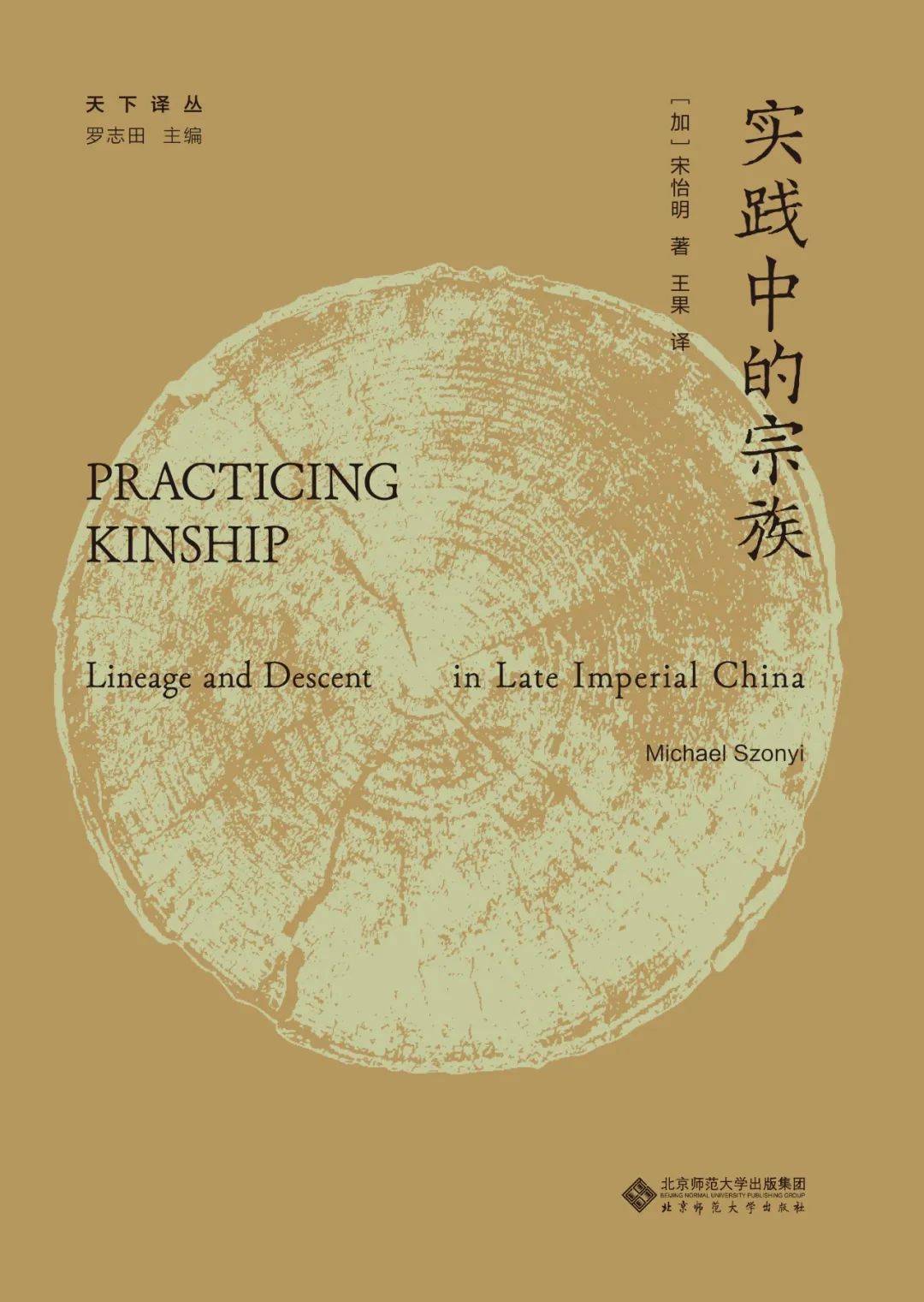
▴
[加]宋怡明《实践中的宗族》
王果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1874年,郭柏苍(1815~1890年),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首府福州庆祝《福州郭氏支谱》编撰完成。他和与其同样有名的兄长郭柏荫一起,兴建了一座壮观的宗祠,修缮了祖坟,并定期到宗祠举行庄重的祭祖典礼。对他们而言,此刻想必是一生中参与宗族活动的巅峰时刻。兄弟俩的这些行为和他们记下的当时的思考,透露出世系与宗族在中国帝制晚期福州社会中的意义。明清时期,宗族的观念以及相关的各类制度和实践,都与它们身处的更大社会语境相关。它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灵活的、多样的,在协商中不断调适。
郭柏苍编纂的族谱,将其世系追溯到一千年前著名的汾阳王郭子仪(697-781年)。据此族谱,郭氏后人在五代时期(907-960年)从河南迁居入闽。元朝时,其后人郭耀定居福清。16世纪,为了躲避海盗侵扰,郭子仪和郭耀的后人、郭柏苍的祖先举起家搬进更安全的福州城内,并定居下来。1842年,也就是郭柏苍编修族谱的三十年前,柏苍、柏荫两兄弟恢复了与福清郭氏宗祠的联系,几个世纪前他们的家族就是从那里分出来的。如同近来关于海外华人返乡的描述,在一篇可能感动现代读者的敘述中,郭柏荫也记述了他艰辛的返乡历程,诸如受到热情接待、与理论上的远亲团聚的喜悦等等,尽管他们之间亲缘谱系还不甚清楚。郭氏兄弟忽略他们与村民族谱上的些许差异,捐资为其重修祖墓、献上祭祀。他们也考察了村中社坛的历史。回福州后,他们还参加了近代世系祖先的年度祭礼。年祭仪式在山腰祖坛附近的祭棚里举行,这个小棚子于1850年重新修缮。六年后,13位郭氏族人共同出资,在福州城内黄金地段购置地产,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宗祠,用以祭祀郭氏宗族远近所有先人。1868年,郭柏荫买下一座盐仓,捐给宗祠,用以维持必要开销。郭柏苍在族谱中强调,祠堂中进行的仪式均严格遵循古代祭祖的重要经典,即伟大理学家朱熹(1132-1200)撰写的《家礼》。
族谱中的多篇序言,均称颂家族对经典仪式、经典价值的尊崇,以及家族世系的可靠。然而,编撰者对于最根本的祖先世系并未达成共识。郭柏苍不得不承认,对先祖是否为汾阳王,他并无确凿证据。在16世纪,郭氏家族第一次编撰族谱时,编者就曾哀恸他们的家谱早在一个世纪前已毁于战火。结果,“元始之开基未得其颠末,支派之源流莫辨其统宗。” 柏苍最终决定,回溯家族近源到元代定居福清为止。但即便如此,他也未能找到可靠的证据,将其兄弟俩与当下的村民联系起来。族谱中对如何进行宗祠里的祭祖礼仪也没有一致意见。族谱中收录的各种规约和文书表明,宗族内部就如何适当地操作仪式有过相当的争论。这些争论最终并非透过《家礼》的原则得以化解,而是都经过了在家族传统和经典原则之间的一番妥协。其中一个重要的争论是关于在新建宗祠中设立祖先牌位的权利。根据《家礼》,排位的序列应由代际和年龄决定。但对于郭氏族人,这个权利已经商品化了,任何人只要只要支付了一定费用,便能取得在郭氏祠堂设置祖先牌位的权利,且只有付费者才能拥有牌位。
郭氏兄弟是19世纪福州社会的领袖人物,下面各章还将证明,他们的族谱也符合晚清福州地区的典型族谱样式。这些文献清晰揭示了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样态和经典所规定的系列原则,包括子承父姓;男方为主的婚姻;追溯五代时期从河南迁到福建来的远祖;收纳宗族,族人需兴建官方样式的宗祠,根据《家礼》的规定在祠内举行仪式;敬拜他们祖先所属里甲社坛演变而成的地方村庙。不过,许多族谱中也保留了与这些男性中心婚姻制度相抵牾的微妙证据,诸如变更姓氏、祖先世系变动不定、宗祠仪式五花八门等等。并且,口头流传的和现流行的仪式,又各不相同。福州地区村落中的长者,还能道出不少男人改过姓,哪些人又是倒插门居住在女方家中等等。在口头传统中,世系往往不是溯及中世纪从河南迁来的贵族,而是某位乱民、海盗或地方土匪。今天村民们所重建的仪式,他们自信和20世纪初一脉相承,但却与《家礼》或王朝官方规定的大不相同。这些再发明仪式中的若干内容,很可能会让朱熹勃然大怒。
福州村民并不觉得应对他们社会中各式各样的宗族和不同说法的宗族历史有多困难,但这对外来观察者而言,确实有些矛盾。本书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这是一本关于帝制中国晚期,即明初到20世纪,福州地区父系宗族组织历史的研究。本书在研究、比较、探寻不同版本宗族关系的基础上,给出整合的叙事,从实践的角度来反思明清时期的福州宗族。明清時期福州的亲属,便是在实践中反映出来。在生活中,人们善用宗族的概念、社会关系与制度。有的要求他的家族某种行为,或者通过撰写文献来推动某种行为,而其他人则对之回应。这些回应,反过来又影响文本和行为的意义,以及这些概念和社会关系是如何为人们所理解的。我使用的“宗族实践”这一概念,主要就是指各色人等如何运用不同的方式,应对、协商和创造有关宗族的意义世界,以及这些意义如何运用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机制上,限制了个人实践的可选范围。通过对“实践”的强调,本书致力于探讨宗族作为一种概念体系、一种制度结构和一种社会互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宗族涵盖着一个场域,在其中关于宗族的实然和应然、宗族的实为和应为等不同概念,充满着持续的竞争和协商。
本书研究的焦点是以父系继嗣为基础的宗族,也就是男方的家族源流。当然,这并非亲属组织的唯一基础,但就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于本书研究的群体而言,这是最重要的。同科大卫一样,我将人类学关于“宗族”定义的争论放在一边,以当事人自称的男性世系概念为准。此法不同于弗里德曼在其影响广泛的中国宗族范式(paradigm)研究,所采用的概念。通过把研究的注意力从统摄宗族的原则、宗族的分类体系转移到资源的控制之上,他在1950、1960年代关于中国宗族的研究,开启了一个中国宗族人类学研究的新阶段。华琛 总结中国宗族的核心标准:“法人团体(corporate group),拥有共同礼仪(ritual unity),以及共同祖先的明确世系(demonstrated descent)。” 这第一条标准可谓天经地义,只有拥有共有产业的合作团体才能成其为一个宗族。而族产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也是理解宗族内部复杂性的重要视角。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物质财产,特别是土地,是中国宗族组织的基础。另一些人类学家,例如孔迈隆和武雅士,质疑了华琛将宗族形成孤立看待的三条标准,批评这些标准将其他的团体打入另册,而其中不乏自称为宗族的团体。本书后面也会证明,即使缺乏共同的仪式和族产,作为父系宗族一员的宣示也是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而且,正如科大卫指出的,在当事人的意识中,族产所有权并不是有关“族”或“宗族”观念的一个核心标准。十分清楚,不管这些群体成员之间还存在其他什么关系,“宗族”和“族” 这些词称的核心在于与父系共同世系有关的群体观念,以及这观念本身被认为是重要的纽带。 对历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晚期帝国的这些团体究竟是何种组织?它们如何兴起?其成员如何表明具有宗族联系?联于宗族以后,对他们有何意义,为何他们团结得如此紧密?
然而,无论宗族怎么定义,没有人会质疑建立在共同世系的群体在晚期帝国的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些文化史家开始关注这种父系亲属取向的起源,或者家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大多数的历史研究更关心家族制度化的课题。杜希德较早为此做出贡献,他认为宗族组织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学家士人的影响,他们为社会秩序应该如何运行设定了一个特殊的图景,藉此将家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大一统、道德提升等更宏大的目标联系起来。伊佩霞将此研究取径充分发挥,她的宗族研究,既关注经典文本,也关注地方人物如何将这些经典文本付诸实践。周启荣的研究认为,宗族组织首先是一种管教机制,借着这一机制,理学家文化精英得以获得社会中的道德领导权,并赋予社会一种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还有些史家看重经济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在宗族形成中的作用,但他们同样倾向于讨论精英的角色。例如周锡瑞和冉枚烁就将精英收宗纳族的举措,视为避免族产分散的手段。白蒂关于安徽桐城的研究认为,宗族组织是某些家族长程战略的一部分,通过联合地投资族田和族学,这些家族试图长期保有精英地位。
华琛关于中国宗族影响深远的定义,旨在将形形色色的宗族制度有序化,并指出20世纪中国华南宗族最重要的特征,但对这些特征形成的历史过程则很少着墨。除非审慎使用,这个定义同样带有目的论的危险,用一个理想型的概念抹杀各地各异的宗族形式。既有研究已经证明,中国各地的宗族制度和观念大相径庭,尤其是在宗族实践的制度上,也会因时空的不同。近来的研究特别关注宗族如何进入地方社会,以及在精英构建宗族之上更大的图景。例如,科大卫对新界的研究,就强调官方的宗族模式渗透到当地社会的重要性,指出这一过程与利益裁处相涉甚多,后者在地方社会中十分普遍。郑振满也注意到,在福建各地的宗族史中,最为关键的是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及财产关系的共有化。陈其南和庄英章则研究了宗族在台湾发展的情况,特别是从一个移民地区到一个定居社会的缓慢转型,形塑了当地的宗族组织。孔迈隆的研究指出,华北虽然没有华琛笔下那种华南的宗族模式,但是家族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村庄社会结构、象征主义和仪式安排之中。这类研究的目的是在特定语境中理解宗族的意义,随着时空的变迁探索宗族制度的改变,体现着带有普遍性的原理在地方语境中的权变。受其启发,本书不意讨论宗族概念的是非得失,而欲在福州这一具体语境中,更确切地说是在闽江边上的南台岛,深入探索父系宗族的丰富维度。
我不用深描的手法详细追述一个村落或某个家族的历史,不是因为个人人类学训练的短板,也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官方在乡间暂住的批准,事实上在研究期间,我在其中一个村子中非正式地居住了好几个月。本书研究路径是由材料决定的。在此研究的早期,我注意到这个地区宗族实践的某些方面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相同的,但却没有一个村庄的材料可以反映所有这些不同面相。在研究中,我的确也碰到有些问题,它们或在文献材料或在口头材料中,都有蛛丝马迹可寻,但在南台的材料中却毫无踪迹。所以我不得不从福州市或其周边地区寻找证据。不过,我认为本书所呈现的宗族的不同面相都是此地区普遍实践的,这不仅是因为明清时期大多数的福州人,大概与其周遭邻里都以相似的方式实践亲属,同时也因为不同村庄的亲属实践,都是对相似的社会、族群和思想等宏观背景所做出的策略性回应。换句话说,本书言及的各种宗族实践形式,都有可能在此地的任何社会群体中发现,也被许多这些群体实行,但在族谱和其他文献中正式记录的、或在口头和仪式实践中非正式展现的,不过是其一鳞半爪。因此,想要得其全相的史家,就需要拓宽考察的范围。
换个角度,即使这更广的考查范围,也会令一些史家不甚满意,觉得还是太过局限。也许有人会质疑地方史对理解中国宗族有何重要、或有何作用。我的答案有二。首先,中国明清时期多元宗族实践的复杂变化,无法仅靠方志、族谱、文集、仪式实践、口述史等某一文类的研究阐明,而是需要综观各种文类及其展现的不同宗族实践面相。其次,只有在其语境中,才能揭示历史材料的丰富意涵,这就要求对材料所产生的地方史作深入研究。我认为地方史是一条最好的路,可以综合考察各种文类,仔细描绘地方经济和社会图景,细致探求地方政治,换言之,是把历史材料讲出故事的好方法。只有在多元的地方语境中对比、研究宗族产生壮大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希望完全理解整个中国的宗族意涵和实践。
聚焦于一个不对应任何行政区划的小地方,也有纯粹现实可操作的考虑。取决于不同的“村落”定义,南台乡间有一两百个村。在1991到1997年期间,我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过几乎每一个村庄。虽然每次到访时间都有限,我也收集或摘抄了50多部族谱,观察了各种仪式,或正式或非正式地访问了当地村民。那些大村庄,还可以一再重访或久住。
通过宗族几个面向的讨论,我认为福州地区人们组织的父系宗族组织,应该视为在受到各种因素交错影响的环境中,个人或群体策略选择及应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普遍的父系社会观念、宗族组织的精英模式及一系列其他变量因素,诸如族群差异、经济商业化、地方精英结构转型,以及特别是对明以降国家关于土地和人口登记制度的回应。当然,这还没有将影响宗族的因素囊括殆尽,不过它们对福州地区而言尤其重要,并且尚未得到史家足够的重视。透过对几个世纪的讨论,我想对中国宗族研究注入一股更强的历史维度。宗族制度和观念的改变,与其所在的物质、文化世界有关,亦与政治社会结构和经济力量的改变有关。通过引入在地方史中自下而上地讨论这些过程,本书对宗族的解释,既不认为它是对家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机械式的贯彻,也不认为是国家或社会精英正统观念的灌输,而是针对复杂多元社会现实,推出的一套统摄人心的正统观念。福州组织化的父系宗族,既不是僵化的,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变化流动的意义之网中构成的。
第一章 福州的宗族观念与制度
第二章 追溯祖源与族群标签
第三章 组织亲属:里甲与宗族
第四章 宗祠
第五章 祠堂礼仪:新年与元宵节
第六章 地方信仰:里甲、宗族和庙宇
第七章 结论:亲属实践的灵活策略
附录 福州地区的宗教碑刻
参考文献
|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