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类学家”,常常想要挑战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谱、祠堂和村民的诉说中,寻找历史与当下重叠的暗影,揭开掩藏在日常背后权力的呢喃低音。
“人家常常问我,你做了几十年南中国的研究,为什么你现在跑到中东和非洲去了。我说没问题的,对我来讲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哪些过程最有意思、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我就去哪儿。”
“人类学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同理心,了解和尊重他人……别让界限定义你,应由你自己定义你的界限。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人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话,你的学术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这也是我从文学中悟得的道理。”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责任编辑 | 李慕琰
视频接通时,萧凤霞教授正坐在办公室书桌前,微微倾身,低头调整电脑的音响设备。
她穿一件白色针织衫,短发齐耳。有人曾开玩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科大卫和萧凤霞说普通话。”采访这天,将近三个小时,萧凤霞始终用普通话作答。她时而微笑,说话轻声细语。

萧凤霞是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任该校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是当代最杰出的华人人类学学者之一。她1950年出生于香港,1960年代末负笈美国,本科毕业于卡尔顿学院,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东亚系硕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人类学名家施坚雅。 (David Ausserhofer/图)
萧凤霞是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任该校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是当代最杰出的华人人类学学者之一。2022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书《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这是萧凤霞第一部中译本作品,内容涵盖这位国际知名的香港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南中国的田野调查和智思之旅。
萧凤霞1950年生于香港一个商人家庭,祖籍番禺。祖父曾在广州经商,后迁至香港,萧凤霞自幼便目睹穿梭往来于家中的广东、香港和外国商人。她1960年代末负笈美国,本科毕业于卡尔顿学院,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东亚系硕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以“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深刻影响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名家施坚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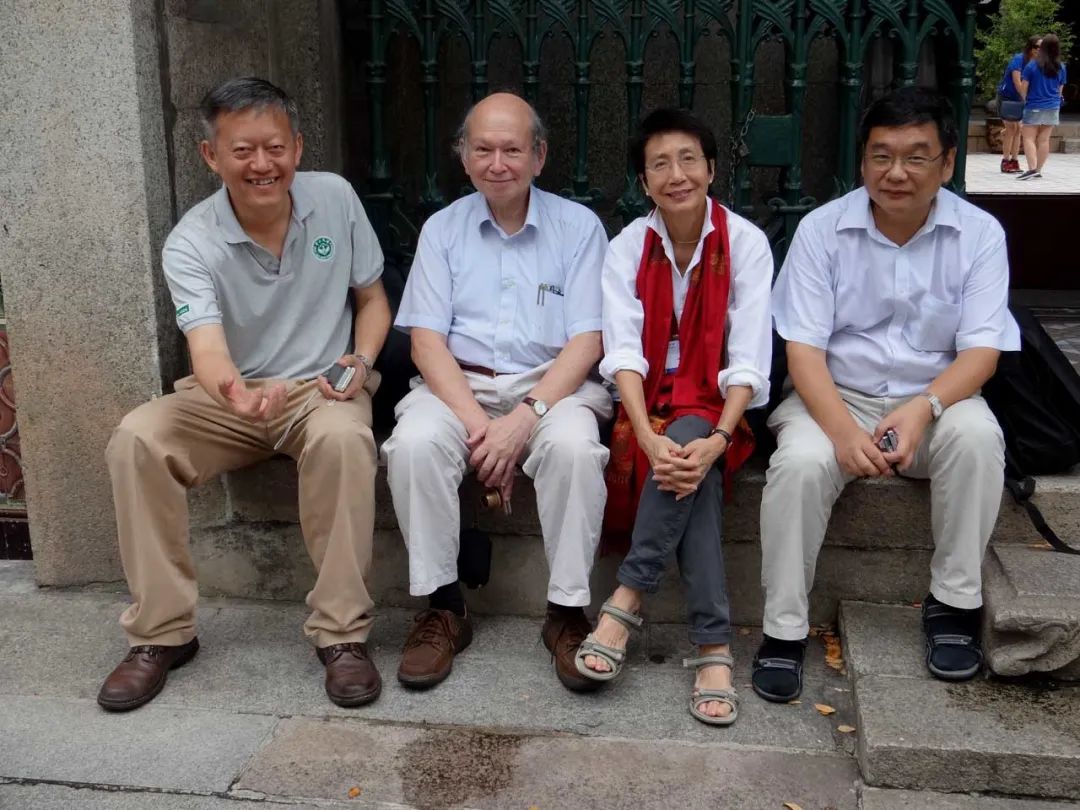
作为1970年代最早在中国大陆从事严肃田野研究的学者,萧凤霞与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等人被视为明清史、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领域华南学派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 (受访者供图/图)
作为1970年代最早在中国大陆从事严肃田野研究的学者,萧凤霞与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等人被视为明清史、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领域“华南学派”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类学家”,常常想要挑战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谱、祠堂和村民的诉说中,寻找历史与当下重叠的暗影,揭开掩藏在日常背后权力的呢喃低音。
四十余年来,她的田野地点从新会、中山、小榄、广州……发展到今天的印度洋、中东和非洲,步履不停。此外,她又对教育界贡献颇多,曾受邀出任欧洲、亚洲和香港多个学术拨款委员会成员;2001年于香港大学创建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推动跨学科、跨地域研究课题。

四十余年来,萧凤霞的田野地点从新会、中山、小榄、广州发展到今天的印度洋、中东和非洲,步履不停。图为2011年在广州的田野。 (受访者供图/图)
著有《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是萧凤霞在耶鲁大学的同事。1980年代,他们曾同在一个供同事参与的读书组中,“起初是想借此机会把堆积案头又未读的书啃掉”,萧凤霞写道。
在这个维持近十年的共同体中,他们同人类学的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社会学的戴慧思(Deborah Davis)以及美国研究、法国史、莎士比亚文学的研究者一起进行跨学科对话和阅读,读书组成员关系密切。在本该专注于民族志写作时,萧凤霞转去编了两册关于文学和历史的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耶鲁的终身教职制度,“斯科特在他的一本书里也宣称,如果他误入歧途,那我们肯定是跟他一伙的!”但这种阅读的探险,孕育出耶鲁日后的农业社会研究课程(Agrarian Studies), 也为她日后进行跨学科研究埋下种子。
詹姆斯·斯科特评价《踏迹寻中》时说:“(萧凤霞)高明地糅合了民族志、社会结构和文化展演的线索,以其湛深学养展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清晰阐明如何援用文化、权力和历史,为华南提供崭新且令人信服的理解。”
反思人类学研究的种子
清晨的办公室阳光明媚,白色的窗框外,一棵大树身躯舒展,有星星点点的绿叶。萧凤霞从香港休假一年后回到耶鲁上课,她已经三年没去华南进行田野调查。“很多大湾区的(田野)项目都停下来了,因为新冠的问题,没办法跑来跑去。”
第一次到广东“跑”田野还是四十多年前。1977年4月,应广东地方政府邀请,萧凤霞同另外九位来自香港的大学教师来到珠三角农村考察。在火红的1970年代,萧凤霞骗导师施坚雅说,“要到广东研究农村的工业化”——实际上却一心奔往华南“找革命”。然而,当她踏进这片土地,看见的却是一片贫穷凋敝的乡村。此后几十年,她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我如此盲目?反思人类学研究的种子从此埋下。
将中国视为一种过程,而非一个地方,尤其关注事物的“结构过程”,是萧凤霞研究的基调。她在几十年间持续深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韦伯式转向,亦在1980年代末完成社会科学思考的大转变——她关注个体在结构中的“共谋”行为,“结构化”与“人的能动性”二者是一个充满张弛的动态过程,“从1970年代非常马克思的观念,变成一个非常福柯的观念,权力关系是辩证的、互动的,每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压迫和反抗这么简单”。
她在《中国作为历程》一文进一步点明了这种思考的变化:“透过一个区域建构的民族志遭遇,旨在挑战我早年受教育、支配20世纪社会科学那些静态、实证的二分法范畴……文化、社会、国家整体、人口、地方等,并不是天生就有、早就存在、不能逾越的实体。相反,它们是由充满经济利益和权力驱动的人的行动及其道德想象而建构的。然而,这些实体往往被本质化为僵硬的概念范畴。”
“理解‘辩证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指的是体味在某个历史拐点,造就这些纷繁历程的多种因素会呈现为具有持久意义且会内化的制度性结构。唯有恰如其分地把社会生活置放在这些历史时刻之中,产生人类行动并赋予这些行动以意义的序列框架才能同等地获得重视。我的人类学直观,往往受这种历史的细致性触引。”
她因此在人类学研究中引入历史的视野,仔细审视笼罩在社会科学中的线性视角,将“过去”带回民族志的“当前”作为分析的核心,而不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视作历史背景。她早期的研究以华南作为实践这种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实验场,考察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被标签为“盗匪和海贼”的边缘族群——水上人“疍民”、华南地区“不落夫家”的抗婚习俗,以及中山小榄镇的菊花会如何在明清以来的各历史交接点成为精英和普通人争夺意义、利益和权力的竞技场。
广东财经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教师严丽君与萧凤霞相识二十余年,十分熟悉她近年来在华南的田野调查。萧凤霞早期的研究以乡村、城镇为主,到了21世纪初,大批打工者进入城市,她敏锐地感知到中国已进入一个大城市的时代。那时严丽君陪伴她在广州城内的不同地方做田野调查,去房地产业刚兴起时的楼盘看别人如何买卖房子,也去广交会、城中村,中产阶级爱去的西餐厅,看人们如何消费食物。
那时严丽君的人类学训练还受以某个村庄或社区为核心的经典研究范式影响,最大的困惑是,“我们怎么不进村呢,我们怎么不每天都去蹲点呢?”随着研究深入,才逐步领会到这样一种看似无边界、无定法,回应多点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见。而在点与点之间,萧凤霞还极为重视历史的层叠关系,在研究城中村时,一度跑去看越秀公园附近有几百年历史的穆斯林墓地。“她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不是守株待兔,死蹲在一个点上等着我们想要观察的事情发生,相反她是很主动、很有策略性地选一些能够回答自己研究问题的点。”严丽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严丽君记得,在还没有被媒体大量关注时,萧凤霞已观察到小北路的非洲人聚居区已十分成型,她们一起去跑小北路、石室教堂、天秀商场、白云区的服装皮具批发市场,2009年左右,萧凤霞已经带着一批全球学者到广州来考察中非关系。“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研究华南地区的跑去研究非洲?其实也是非常自然,因为那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她敏锐地捕捉到这些研究的价值。”
一次在贵州山区做田野,严丽君在晃晃悠悠的客车上睡着了,突然车停了,有村民在路上摆摊挡了路,严丽君刚回过神来,萧凤霞已经下车去和村民交谈。严丽君很惭愧,萧凤霞比她年长很多,却从未关闭探索的闸门。
在城中村做田野时,萧凤霞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维持了十余二十年,从陌生人变成了老朋友,严丽君称之为“细水长流的田野”。她记得和萧凤霞多次去一位老人家里拜访,从最初对方健在,到一起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再到儿子生二胎、三胎,直到老人去世,萧凤霞没能赶上参加他的葬礼。
“我们研究的历程和他们生活的轨迹、他们家庭的生命周期都交织在一起。”严丽君说,“这个漫长的变迁的故事,本身就是特别的神奇,特别的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美妙。”
“她一步一步走过来,走过很长的历史”
萧凤霞被视为较早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在中国付诸实践的学者,但这也是她与研究华南地区的历史学者多年合作的果实。在这一取向上,历史学的研究,则有赖于刘志伟、郑振满、陈春声、赵世瑜、科大卫、程美宝等学者的倡导与多年耕耘。
在学术界,“华南学派”一词最早并不是一种自我称呼,而是中国内地以北方地区传统史家为主的学术界,对一批1980年代初以来在华南地区从事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海内外学者的称呼。更重要的是,它并非一种地理区域意义的概念,而是一种学术取向或学术主张。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现任所长宋怡明师从科大卫,被视为“华南研究”的第三代学者。他曾解释,“最大的误会在于很多人以为‘华南’指的是地域。很偶然,早期的华南学派学者,大多数在中国南方,逐渐发展起这么一种学术主张,它强调田野调查的方法,重视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等民间文献的使用,自下而上看历史。但是,这些方法当然不是只有在南方才能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曾在《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华南研究30年》一文中介绍“华南研究”形成的背景——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海外的大部分中国研究学者,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于是他们多在中国香港新界、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特别是新马地区的华人社区进行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田野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学术视域和理论方法。
由于这些地方和福建、广东地区有很深的人文历史渊源,当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放伊始,承接着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进入中国大陆,自然首先进入福建、广东地区,与当地的一些学者有了合作关系,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并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中国大部分省区。
从1977年春天到1980年夏天,为了开展博士论文研究,萧凤霞频繁来往于香港与广东新会之间,不断造访新会、江门和广州等地,拜访公社和大队企业,跟一些基层干部和工人打交道,吃着水果交心夜谈至深夜。从1980年代开始,她开始和陈春声、刘志伟等人一起在华南的田野上行走,她形容这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神州南人”,“1970年代是我一个人跑田野,1980年代我们几个人走,1990年代我们十几个人走,到现在是没法计算了”。
在此过程中,这批学者产出了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比如科大卫的《皇帝与祖宗》《明清社会和礼仪》、萧凤霞的《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陈春声的《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等等。
萧凤霞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最早和陈春声、刘志伟一起跑田野的故事。她向他们学历史,他们向萧凤霞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前卫的社会科学理论。那时常能看出两个学科的不同,“他们喜欢问这是什么东西,我是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有时和老人家谈话,问来问去,刘志伟觉得有点奇怪,萧老师我们族谱都拿到了,你怎么还在重复问,“我说, 你看他们讲什么跟没讲什么同样重要。同时,他们讲什么、怎么讲也同样重要”。
后来刘志伟和萧凤霞两人曾合写《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一文,“有一次我们在田野,(陈)春声骂我们两个,你们做那些族群研究,宗族、祠堂都变虚了,族谱都不可信了,那么玄的。可是过一阵子,他研究那些深山里的地方神明,都讲得越来越玄了,他自己也变了”。
《踏迹寻中》的封面是1980年代初,萧凤霞在广东新会做田野时用十元人民币在县城相馆买的一张本地摄影师拍的照片。一位挑担的华南妇女从充满新会特色的葵林深处走来,树林中透出的昏黄阳光洒在这条小道上。萧凤霞十分钟爱这张照片。“有一点光,她一步一步走过来,她走过很长的历史。一张照片中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1994年,在广东新会潮连的地方节庆仪式。 (受访者供图/图)
近年来,萧凤霞的兴趣集中于怎样从概念、理论上理解世界中的亚洲。“我着意将研究对象视为置放在世界组装的组成部分,而它们是由纷陈的文化意义和权力场域所锻造的。”而文学则让她关心人性,关注权力的语言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推衍至人的身心。她主张用一个比较批判的角度去看人这一个体是怎么被定义的,又如何能超越一些定义,重新去检视自己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否则,我们以为的选择都不是自由的选择。
在我们的采访中,萧凤霞不断重申着打破区隔、边界、标签的意义。在香港成长的经验,塑造了她不断打破学科范式、不被边界所束缚的学术视野。
以下是根据萧凤霞教授专访整理而来的访谈
“在香港这个小地方,看到一个大世界”
南方周末:你过往的资料中个人故事较少,可否先聊聊你的家庭和成长?
萧凤霞:我的家庭可说是“老香港”了。爷爷这一代从广州到香港做生意,爸爸在香港出生,跟妈妈在香港结婚成家。我常常说香港“背靠岭南、放眼世界”,它是一个充满本地色彩的地方,但同时又背靠岭南的文化、历史、社会,而且跟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三而一的有机整体,三个部分都有,才变成这样的地方。
这个过程可以从我的家庭历史中得到反映。祖父从广东到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爸爸带家人到澳门避战,战后才回到香港。我从小就看到外囯人来我们家做客,我的姐姐们在1950年代已经去了英国念书,我们这些年纪小的之后去了美国。所以你看得出来,一个家庭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世界,跨越了文化、地域、阶层,甚至跨了种族,我好几个姐姐和哥哥都是跟外国人结婚,所以我们下一代有很多跨种族的小孩。
这样一个不断跨越边界的过程,不仅是地域的,还有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阶层的。不只是我们的家庭,很多其他香港家庭都是这样。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当然有很多本土的东西,背靠岭南,也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一个地方,从头到尾都是动态的,很难去标签这是什么文化或地域。同时,也不是说你土生土长在香港就是香港人,因为很多外国人也长居香港,一住就是多年,他们带来很多世界的东西,回老家也带回很多香港的东西,他们来来去去也都变成香港人了。
所以不能把香港看成是一个(静态的)地方,而是一个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很多人的生活都在里面,也同时带着那些生活经验到了世界各地。这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我这是用香港来举例,北京人、上海人、山东人,都可以这样去做。人家常常问我,你做了几十年南中国的研究,为什么你现在跑到中东和非洲去了。我说没问题的,对我来讲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哪些过程最有意思、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我就去哪儿。我还是研究中国,可是现在在非洲、中东去研究,你把中国变成一个过程来看的话,就多了很多研究的题目。
南方周末:你在香港成长接受的教育是怎样的?
萧凤霞:我这一代人很多都是在教会学校上学。我们念英国文学、法国历史,也学中国历史,这是非常精英的。因为我们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成长,教我们的老师大都是因战乱来到香港,当时工作(机会)不是太多,所以很多非常好的学者当了中学老师。令我对历史产生兴趣的黄维琩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学问和修养的书法家,你看我们中学就是让这些人教导的了。同时我们的英文是从英国来的老师那里学的,读英国大文豪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就是莎士比亚。
在香港这个小地方,却能看到一个大世界,这些都变成我们的日常。所以1997年香港回归前,人家问我如果要在中环设置一个回归广场的话,应该放什么东西去纪念呢?我说什么都不放,因为香港就是这样包容、自由、开放的空间,这才是香港的精神。
“从头到尾都是华洋杂处、互相互动的”
南方周末:听说你是从父亲那里学来令你引以为傲的“西关话”?
萧凤霞:我的广东话是跟我爸爸妈妈学的,而爸爸则是跟祖父学的。以前我不觉得这是西关话,可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程美宝教授还有很多人说,你和你姐姐一起说广东话是特别清脆幼细,特别好听。我想这跟西关话是怎么来的有关。18到20世纪,很多福建、广东的大商人在广州城西定居下来做生意,规模很大,也跟外国人有很多交往。
程美宝教授说, 所谓的“西关音”(West End Speech)是指广东省城以西自18世纪伊始商人聚居的一带所流行的粤语口音,这种口音被称为“西关音”或“西关话”,逐渐成为“标准粤语”。因为那些行商非常有钱,他们的女儿叫做西关小姐。(注:程美宝在《城市之声西关音:由省至港及沪》中提出,18至19世纪,广州的都会气息是在城墙以外酝酿的,这很大程度是因为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唯一一个可以从事西洋贸易的口岸,“西关音”是辐射至香港、澳门、上海和世界各地粤人社区的“城市之声”。)
你看广东文化其实是非常杂交的。广东话里有很多惯用名词是从英文转过来变成广东话的。比如保险业——insurance,我们老一代人叫“燕梳”;邮票——stamp,我们叫“士担”。程美宝教授告诉我粤剧也是如此,它结合了不同地方传统发展而来,音域很广,光用二胡不够,所以粤剧很早就用西方的小提琴,音域大很多。对我们来说,广东文化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很多地方的传统文化、有意思的东西,都可以合起来,就是这样有机的。
香港开埠之后,很多人都去了做生意。冼玉仪教授写过一本关于东华医院的书《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权力与慈善》),在19世纪后期,香港有一个慈善组织叫东华医院,有不少与外商做生意的商人组织,总部在香港荷李活道的文武庙附近,他们在香港、澳门、广州和其他中国和东南亚的城市,都有生意和亲属网络,省港澳的商业往来一直是很密切的。
我们现在在香港大学的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有一个研究项目叫Delta on the Move,可以叫“动感珠三角”,就是要把这个地域的变化讲出来,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慢慢地看,不同年代,不同大环境、小环境,那些人一起做出来的区域和文化,从头到尾都是华洋杂处、互相互动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珠三角这个区域会呈现出这样的特质呢?
萧凤霞:我想因为跟水有关。珠三角从头到尾就是西江、北江、东江一起合起来变的嘛,水是非常流动的,人也是非常流动的,货也是,思想也是,文化也是,整个社会不像北方黄土地那样固定在乡土。与此同时,珠江的水跟南中国海、印度洋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看南中国海,过了东南亚,到了印度洋,一直往西走,我研究的地区就是从头到尾用水域把自己的生活跟世界连在一起。很多做生意的都是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的贸易制度,不同做生意的方法加起来的,没办法标签他们,这个地域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在“华南”这个概念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一个更宽广的“中国南”(China South)的天地。这是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的提法,他说我们看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常常看成东西之分,是错的。 以中国来讲, 根本的分界是南方和北方, 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一个是黄土地,农的、内向的、封建的,南方是水的、动态的,跟世界已经有悠长的关系。这南北之分,比东西之分更要厉害。
“放在一个有机的大环境里,这就是很自然的”
南方周末:亚洲互联是你近年来关注的重点之一,能不能谈谈这个研究?
萧凤霞:前几年我跟两位历史学者,也是我的同事,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和康奈尔大学约翰·斯坦博历史学教授泰利可佐(Eric Tagliacozzo)编了三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叫做《翻展亚洲》(《Asia Inside Out》)。
亚洲,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这些都是我们基于地域给的标签和分类。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实质,因为从很久以前,人、货、价值观、制度,都是一直在流动,跨过了那些地域分类。第一本书讲的是连接时刻,第二本讲在什么地方连在一起,第三本则事关那些流动的人怎么去创造连接。
2019年我在清华大学做过这套书的讲座,很多人来。第一本书的封面是一个16世纪的画作,由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收藏,你看到里面有中国商人、一个中国女子,也有一些蒙古军队、中东商人,还有一些盗贼,整幅画讲到历史丝绸之路上族群的多样性。第二本书的封面是我自己拍的印度洋上阿拉伯人用得最多的船只,从唐代一直到现在都是用来运货,而印度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地点。最后一本书的封面,背景是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那里每个星期天都有很多印尼籍的家庭佣工在聚会。
表面上他们都是有点out of place——就是你本来不会想到这些人或物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历史的例子,你有没有去过广州南海神庙?听说建在隋唐。这个庙现在已经是个大旅游点,放着很多神明,有一个黑黑的大胡子穿着官服,可以看得出来完全不是华人。这可能是唐代,有大量印度和中东的商人来到中国沿海,比如泉州、广州。我猜这个大胡子来到这里之后,船走了,他一直在等船来,可是没有。他死了以后,附近的村民还去拜拜他,也有清代学者去讨论这个人的由来。
这就是一个object out of place,这个广东的南海神庙不是小庙,是朝廷认可的,有很多封号,为什么这个大胡子会出现在那个地方,还穿上中国的官服?要是你认为在一间中国庙宇里,穿着中国服饰的神像就必然是中国的,那么这个大胡子便显得“格格不入”了。
另外在马来西亚槟城,我们去过一个田野。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祠堂,守在门口的石像,是印度的锡克族人的形象。很多华人的坟墓,也有这些小小的锡克族人的石像去守护。为什么会这样呢?要是你把它们都放在一个非常有机的大环境里,这就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那些地方都是“连”在一起的。
“别让界限定义你,应由你自己定义你的界限”
南方周末:你在香港的家庭历史、成长环境和你日后的学术性格有关吗?
萧凤霞:刚才讲到,我在学校是这样,在家庭是这样,语言也是这样,有一个非常多元的成长过程。这样对我以后的学术追求可能有一定影响,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最开始我想念英国文学,可是后来变了,念了社会学。我在斯坦福念硕士课程时,导师是一个经济学家。那时候就越来越觉得20世纪的社会科学有问题,就是没有以人为中心,很精准,可是没有了人的味道,慢慢我就转了去念人类学的PhD。
我始终对20世纪的社会科学,那些他们用来定义研究的项目都非常怀疑,常常就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它们拆解,重新再合起来。程美宝常常说我的思考是非常出格的,我就爱挑战那些既有的范式和范畴,让很静态、很有限制的标签,变成非常动感的,不是线型的历史观。就是把那些比较机械化的思维拆开,然后把我觉得是真实的人的经验,从看到的表面的(现象),(深入)到了人性的哲学问题,重新去想。那就是我的学术追求。
南方周末:具体而言,这种学术性格是怎么体现的?
萧凤霞:当你是那么动态、有那么多的空间探索的时候,你看的东西可以是很基本、很普遍的,也有很实在本质的东西,区域的东西,大时代的东西,怎么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为什么我这本书取名Tracing China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中国也是,看世界也是,你从表面的东西一层一层地探讨下去,很多平常看不出来,被遮蔽的东西,慢慢就浮现了。
(注:萧凤霞曾和南方周末记者讲到一个故事。改革开放之初,她和刘志伟在广东的镇上做研究,时值新年,那时没有手机,他们去邮局给各自在广州和香港的家人打电话。到了邮局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告示上写着:按上级指示,我们现在可以邮寄贺年瓜子。“我一看就说这是什么,这样的事情都要按上级指示?是不是太过分一点。可是当时刘老师不明白我在笑什么。他觉得理所当然,没有感觉到权力的语言已渗透到他的身心。正是我们的成长背景不同,视角不同,才有不同的反应。”)
南方周末:你在社会科学中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注,是不是和你对文学的爱好有关?
萧凤霞:是的,我一直都很爱好文学。乔治·奥威尔有一篇非常短的小说叫《绞刑》,是中学时一位教英国文学的老师让我们看的。那时我十五六岁,没有感受,也不太明白作者在故事里表达的人生哲理。几十年后我在耶鲁教书,我的一个博士生说要找一篇短的文章给学生看,教他们如何写作,便选了这篇文章。这次我再看的时候,深深地被震动,当你经历过人生几十年的起起落落,你会觉得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非常宝贵的。这就是最厉害的文学可以做到的。
除了奥威尔, 还有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讲一个学校专门去培养一帮年轻人作为实验体,用来生产人体的器官。这本书就是讲那些被商品化的人的成长和死亡,我读完以后心情难以平复,因为最后有三个这样的人,他们产生了感情,很难受的,这些就是很好的文学,可以想象到未来是怎么样的。
最近《明报》的一个访问,我跟(做访问的)年轻人说,你可以把顾城的一首诗写进去吗。这首诗叫《感觉》:“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
这是我想送给现在年轻人的一首诗,你们是有生命力的。鲜红就是你的passion(热情)、你的empathy(同情),淡绿就是你的思考,两个都要。
南方周末:你有思考过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什么吗?
萧凤霞:我觉得人类学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同理心,了解和尊重他人。另外,就是我常常讲的——Don’t let boundaries define you, you define your own boundaries,别让界限定义你,应由你自己定义你的界限。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人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话,你的学术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这也是我从文学中悟得的道理。
|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