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关于婚姻关系的构造,并非基于平等人格的男女感情的结合,其主要将妇女视为夫之附庸,所以对清代“离异”案件的讨论,不能忽略另外两种案件类型即“典妻”和“卖休”:前者是为获取钱财,暂时结束婚姻关系,但保留回赎的权利;后者则类似于“绝卖”,为获取钱财而将妇女休后嫁卖。因此,对“离异”案件的讨论也要将这两种结束婚姻关系的案件类型纳入。更为重要的是,清代律例中对唐律延续的因“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妻对夫的谋害罪)而强制“离异”的在实际中几乎没有踪迹,法律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夫典雇其妻、夫将妻卖休(离婚买卖)、夫强迫或默许妻与别的男人通奸,法律一般对此会强制离异。

(一)“典雇”妇女:“礼义”与贫困
在关于清代县衙对卖妻案件审判的研究中,苏成捷敏锐地发现“妻子买卖与小农的土地买卖存在着一模一样的用语和很多类似的行为,包括典卖与绝卖之间的区分,还有要求找价的行为”[1]。在他看来:“这些有关土地买卖与卖妻的共同用语,以及在卖妻案件里发现的找价要求,似乎反映了小农对于妻子的态度基本上是类似于土地的心态。土地与妻子都是如此重要的资产,因此无法与己身绝对分离,不管这种转移表面上采取何种形式:它们与个人之间有一种基本的关联存在,关涉着个人的地位、认同与生命,是不可能借由交付金钱而完全斩断的。”[2]不过在该文中,苏成捷并没有就具体“典妻”案件进行讨论,因为他发现妻子买卖很少明显冠上“典”的字眼,在他的分析样本里,“县级司法档案里没有一件提到‘典卖妻子’,而在刑科题本里只有一件提到‘典卖妻子’”。[3]
事实情形确实如此,笔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到的刑科题本中,只有四件明确提到“典妻”,除去一份满文档案涉及一位满族旗民因为“典妻”,被认为有辱满人脸面被专门上奏要求对其进行惩罚外,其余三件案例均为汉文。然而,未明确含有“典妻”字样,并不代表着此种行为在社会实际中少见。
相反,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在社会实际中较为普遍。当时甚至有官员专门就此向乾隆皇帝上报,要求严厉惩处,以此宣扬“礼义”教化。乾隆时期四川重庆镇总兵张士庆,就向皇帝上呈奏折,要求“严查奸蛮典雇妇女为娼事”。在他看来,“典妻”尽管是贫民在生存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终究“有伤风化”。若不严加管理,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查川省茂州、汶川、保县等处在万山之中,地土贫瘠,米粮稀少。每年九十月间多有蛮民携妻来重,于城外河坝空地打棚盖茅棚佣工觅食,约计百余户,或至二百余户不等。至春暖方归,内有一等无耻奸蛮,于彼典雇妻女,混杂居住处卖娼作活,岁以为常相。乾隆二十年四月内奉谕旨令前任抚臣转饬实力稽查,实系佣工力作之人,仍听其往来居住。若携带不良蛮妇有关风化,即行逐回。臣任期后又按期派发官员稽查,如遇到蛮民生事为匪,就立刻稽查讯问。并令商民不得擅自去往蛮民居住地方,兵役不得借机滋扰,防查严密。如遇个别奸蛮之徒,伤害风化,立法驱逐,以靖地方。但查茂、汶至重庆往返程途不下四千里,穷蛮远涉,资釜艰难。若果听其远来又将其驱逐,不如与本地方先行查禁,免令长途往回。
因此,恳请皇上勒抚臣转饬地方官,预期严行谕,设法稽查,如果奸徒仍有典卖妻女,携带出外,即行查拿,分别纠处。私自潜携带出境,饬令沿途文武官员一体盘查,回原籍收管,于风化有益。受人典雇之妇固非善类,其他妇女虽非俱系典雇而来,但千里长途男女混杂,难保其尽守妇道,俱属善良。且奸蛮携妇女外出,绝不会自露出典雇妻之情,而所在盘查之处亦恐不能逐户查出竟无一二遗漏。查此等不良妇女大概俱属年少之人,以后是否可除年至四十以上蛮妇,仍听携带出外佣工、往来居住不禁外,其年少妇女,悉行禁止,不许仍携远出。则不良少妇既难混远行,而奸蛮雇妇为娼之处将不禁而自熄(息)。[4]
张士庆的上奏不无迎合乾隆“教养”理念的企图。公元1735年,刚登上皇位的乾隆皇帝就曾发布了一份谕旨,明确表明了他的“教养观”:“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盖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广其怀保,人君一身,实亿兆群生所托命也。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惟期顺天因地,养欲给求。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5]乾隆在这份谕旨中,着重要求所有官员都应当重视“教养”百姓。[6]
作为总兵,尽管张士庆认识到这些贫民因为土地贫瘠而缺衣少粮,逼不得已才“典雇妻女”,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养民”而是“教民”。在他看来,这种“典雇妻女”的行为违背“礼义”,有伤风化,应该严格查禁。他在上奏中反复使用“奸徒”“蛮民”“固非善类”等词语指称那些“典雇妻女”的贫民,认为对这些违犯“礼义”的底层民众,就应使用严格手段进行管理,否则他们会扰乱社会秩序。不过,他忽略了“教民”的基础在于“养民”,对于深处生存危机的底层民众而言,“典雇妻女”亦实属无奈。
对“礼义”教化的重视实际上亦是对社会的控制:这些底层民众数千里辗转,混杂居住,显然影响社会秩序,难于控制,强调风化和“礼义”,要求民众皆应遵守“礼义”,将其限制在家庭秩序中,则易于对社会的控制。正如一位刑部官员所认为的那样,“犯奸”的行为应该遭受惩罚,“盖名节乃举世所重,奸淫为恶之首”,因此要“惩邪淫而维风化!”[7]在当时诸多官员看来,法律应该通过惩罚这些犯奸者,在社会中创造一种压力,如此才能有效维持社会风化。
然而,对于深处贫穷现状的妇女而言,除了“典雇”自己,似乎也难有更好的生存方式,四川巴县档案中有不少显示出当时贫穷的妇女因为生存处境艰难,生存心态较为脆弱,容易选择轻生。

妇女戴氏因为丈夫徐曰泰常年外出,在家贫困没有吃的,自缢身死。[8]
彭光德的妻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因在彭来仪、彭安相父子家中借钱不遂,自缢身死。[9]
王文弼与朱曾氏通奸,王经常把家中的物什悄悄偷给朱曾氏,以致王文弼的妻子陈氏时常因此与王争吵。一日,陈氏用棉纱换来一匹布放在家中,却被王文弼悄悄拿去,陈氏知道后就把布拿回,还斥责朱曾氏无耻,朱曾氏当晚就轻生自缢。[10]
“礼义”对于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底层妇女而言,无助于改变其生存境遇。妇女选择“典雇”与人,往往是为了生存。
宁波鄞县人施淦友于光绪九年(1883)二月间,凭媒人张应氏典买寡妇庄应氏为妻。十年春,施淦友因病失业在家,家贫难度,庄应氏私回前夫家居住。六月二十日,该氏来施家捡取火钳,没有找到,于是就向施索赔,二者发生了争吵。庄应氏收拾衣物要求回家,二者发生了争吵,施淦友用木棒殴伤庄应氏致死。庄如丙是庄应氏的儿子,庄如丙供:“已死庄应是母亲,父亲已故,光绪九年二月,母亲因未孀居,小的年幼,小的无人管顾,自愿典与人为妻,由人作媒与施淦友做女人。当得身价洋银六十圆。言明两边来往,十年后仍回小的家过度,当就过门。和施淦友并无嫌隙。母亲乘外出,私自走回,施来接过几次,母亲不肯回去。后来想到遗忘了一把火钳取回,没有找到,于是就和施产生了争吵,施淦友用木棒把母亲打死。”[11]
妇女选择“典雇”与人,一般程序是由媒人见证,双方订立典契,约定身价银和典期,妇女暂时与夫家结束关系,嫁到典主家,出典者由此获得一笔钱财以养活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庄应氏因为丈夫已死,子女无人照管,因此选择“典与人为妻”获得一笔身价银。庄应氏并不希望与夫家完全断绝关系,因为若选择改嫁的话,庄应氏就失去了对子女的监护权利,这对于一位母亲而言,显然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庄应氏约定十年后仍回前夫家,只是暂时嫁到施淦友家。无奈施淦友亦十分贫穷,庄应氏就想私自回到前夫家中,这对于施淦友而言显然难以接受。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已经出钱将其典雇作为妻子,庄应氏就不应私自回到前夫家中,将庄应氏视为自己的所有物,这种心态恰如前述苏成捷所认为的近乎将妇女视为土地的心态。然而妇女并非土地,其内心情感以及与夫家的关系亦非说断就断,在此种困境中,庄应氏最终丧命。
这种将妇女视为男子附属物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买卖双方为妇女的身价银争执不休,甚至由此闹出命案。此类案件就如土地买卖引发命案一样,双方在价银数额问题上互不相让。妇女可以像土地一样典雇与人,男子在意身价银甚于妇女处境本身。以下两个案件均是由“典雇妻女”身价银争执引发命案。
金潮福籍贯是海宁州,当时在四川生理,娶妻于氏,生有两女。道光十一年(1831)的时候,金回到杭州,但是他的妻子女儿仍然在四川。这年的十一月,金潮福凭靠不知情的媒人陈氏作媒,娶了孀妇朱氏为妻。十二年的十月金仍然要回四川,朱氏无人收管,托徐氏为媒,议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立有典契。徐玉燕付过洋钱六圆,尚欠钱十四圆,金潮福屡次讨要都没有给,于是在道光十三年的五月初九黄昏时分,邀同徐玉燕相认识的徐老大,金潮福与徐玉燕混骂,用刀将徐扎死。朱氏供:“妇人先嫁董在玉为妻,董死后又嫁给了金潮福为妻,金先在四川生理,娶有妻室,寄居四川,道光十二年金仍然要回到四川生理,就把妇人典与徐为妻,徐氏为媒,立有典契,说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同妇人一同寄居在别人家。十三年的五月初九,妇人闻到吵架声就出来看,看到金潮福已经把徐有玉戳倒在地,妇人把徐扶起到床上,不料徐有玉就死了。”金潮福用刀戳伤徐玉燕身死,法律判决“应如该抚所题,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并绞监候”,媒人“徐氏知情应照嫁娶违例,媒人知情减一等,杖七十,照例收赎”。朱氏则照律离异归宗。[12]
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间,江云生因为患病没有钱医治,就自愿把妻子典与叶锡其为妻,当时付钱三圆,把妻子领回家过门,并且约定十年正月付清。江云生因典卖妻价与叶锡其发生口角,叶锡其被江云生用刀砍伤身死。法律判决江徐氏应归宗,由亲属家领回,典价洋银照追入官。[13]
以上两个案例皆反映了妇女在“典妻”交易中的被动和从属地位。在前一个案例中,金潮福并非由于贫困,而是其娶多妻的行为不合“礼义”,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当他要回到川地,就将后娶的朱氏出典。滋贺秀三已经指出,传统中国婚姻关于妻之名分是独占的、排他的,法律禁止一个男人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子:“夫与妻被一对一对应比喻为日与月、天与地。法律也处罚有妻而又娶者,并且认为后婚无效。”[14]无论金潮福选择将朱氏典出还是直接“卖休”,都意味着金潮福将朱氏视为自己的附属之物:当其回到生理之地时,他可以选择将朱氏典出,以此获得一笔钱财;当他再回来时,又同样可以用钱财将朱氏赎回;金潮福又因身价银而起争执,其在意身价银甚于对朱氏的处境。
在后一个案例中,男子因为无钱医治疾病,就将妻子视为财产而出卖,以此获得一笔钱财,后又因为身价银而酿成命案。无论怎样,在“典妻”关系中,男子将妇女视为从属物品的心态都较为明显。
对于身处贫困处境中的妇女,与男子相比,其生存境遇更为艰难。妇女无法像男子那样外出佣工,又没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土地,在此种困境之下,或许身体是唯一可以出卖的“财产”。对于那些因贫困而娶妻困难的底层男子,妇女的生育功能可以将其家族延续。
法律和意识形态强化了身处底层的妇女自身将其视为男子之附属物的观点。法律关于婚姻中的妇女地位的规定,可以看到“夫权”的强势,妇女在此种情境下,反倒将那种视妇女为男性的附属物的观点作为理所当然。从朱氏的供词中以及这两件案件中妇女均同意被典的做法,可以看到妇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那种将其视为附属的观点:“就把妇人典与徐为妻,徐氏为媒,立有典契,说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这种不合理,对于身处当时情境中的参与者似乎一切自然而然:有关“礼义”贞节的意识形态塑造了“顺从的妇女”,妇女以听从丈夫的安排为“美德”;妇女被排除在经济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妇女的职责主要限于家庭空间,妇女的家庭责任服务于整个家庭经济活动。当整个家庭因为贫困而无法生存,丈夫就将妇女视为“物品”令其流通,那些长期顺从的女子即会听从丈夫安排。

刑科题本中对违犯“礼义”的“典妻”或“卖休”行为,皆依照律例判决。以上两个案例均显示法律强制妇女“离异”,严格比照律例规定。对于朱氏,法律则要求“离异归宗”,不会考虑到朱氏归宗后的现实困境。同样,对于江徐氏亦是如此,要求亲属领回。
若妇女父母双亡,无家可归,情形会相对复杂。法律对妇女的判决,一是官府作为卖方,将妇女交由官媒嫁卖,财礼银入官;或者由前夫、后夫一方领回,不过这也并非出于对妇女弱势境遇的关怀,仍然是首先考虑到“礼义”,因为担心妇女再次改嫁。
道光十二年(1832),张氏因前夫死后不愿意守寡,自愿改嫁,嫁给颜恭钲。但是张又嫌弃颜贫困,于是回到母亲族家居住,颜多次接其回家均不回,于是颜将其卖休给瞿式练。族人颜恭前遇到颜恭钲,斥责其不该卖休,有辱祖人脸面。二者发生争吵,颜恭前失手用刀砍死了颜恭钲。张氏则“合依用财买休卖休本妇杖一百律,杖一百,系妇人照律收赎”。法律考虑到“张氏父母俱亡,无宗可归,若断令离异,势必复行改嫁”,最后“仍令后夫瞿式练领回”。[15]
强制“离异”后,妇女为生存有可能选择再次改嫁,这与清代鼓励妇女守节重视“礼义”的理念不合,因此会判令由前夫或后夫一方领回。尽管法律实践对现实有所适应和妥协,但并非出于对妇女现实境遇的考虑,仍然着重考虑的是“礼义”。
(二)“卖休”案件中的妇女
与“典妻”类似,“卖休”也是为钱财而结束婚姻关系,不过前者是暂时结束婚姻关系,后者则类似土地“绝卖”,将妇女嫁卖给买主。“卖休”的一般程序也是凭知情或不知情的媒人,联系到买主,议定身价银,并由媒人作中人,交付银两且写立卖契或休书后,由买主娶回。
此种为获得钱财而将妻子嫁卖的行为显然违犯清代的“礼义”,因此官府若发现的话,一般会要求强制“离异”。此种为获钱财而休妻的“离异”形式在社会实际中也较为常见。笔者在乾隆朝“朱批奏折”中就发现了一份乾隆十五年(1750)湖北按察使德文针对“卖休”案件请求严惩媒人的奏折。在他看来,“卖休”行为违背“礼义”和人伦,有伤风化,应该严加管理,以正教化。兹录于此:
夫妇为人伦之首,婚姻之礼义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楚北愚民廉耻道丧,因贫卖妻,恬不知怪。夫离别为人生最苦之事,百年夫妇一朝活拆。母去,子当牵衣涕陨,恩缠爱割,回首悲啼。小民岂独无情,乃忍出此!遂当心访察,始知楚北有等棍徒平时专以媒合作生涯,见人贫困,花言巧语诱其卖休。见人愚鲁,嘴枪舌剑鼓其买休代写离书,捏造庚帖。灭伦伤化之事,顷刻而成。从中索后手索媒金索酒食,不厌不休,可怜贫民卖妻银两半入奸徒之手!若无乡邻族党并无此等惯媒,即人起卖休之念,而妻不比货物可以出售。而买休之人,亦断不敢向夫妻好合之家叩问卖妻与否,是买休卖休皆惯媒设局哄诱而成是也。楚省如此,他省或有类此者,均未可定。
奸徒忍心灭理至于此极,若不设法以示惩创,则伤风败俗,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愚民被哄,情尚可悯。惟惯媒原非四民艺业,当此升平盛世,何事非谋生之具?乃必拆人婚姻离人骨肉,以致败坏风俗!欲止活拆之风,当严惯媒之罪。请嗣后有知情为媒,活拆人夫妇者,照和同相诱卖良人为妻妾律,问以杖徒。使奸徒畏法不敢惯作媒合之人,则买休无线,卖休无门,活拆之风不禁而自绝。[16]
事实上,这位湖北按察使对待“卖休”的态度较为暧昧。他既看到了“卖休”往往是贫苦民众为生存而不得已为之,但又认为为获取钱财而休妻的做法终究违背人伦情感,有伤风化,要严加管理。所以他不是建议惩罚那些“卖休”的夫妇,而是选择将矛头针对那些“惯媒”。在他看来,夫妇离别,子与母散,这是“人生最苦之事”,颇值同情。身处底层的贫苦百姓,并非无情,他们亦非仅因贫困就会将妻子嫁卖。“卖休”现象之所以相对普遍,主要是受那些“惯媒”的挑唆,这些媒人属于巧舌如簧的“奸徒”,看到贫困的民众,就诱使他们将妻子嫁卖,对于鲁钝的老实人,甚至还代写休书。然而贫民卖妻所得的身价银,往往半入这些媒人的手中。他们还不厌其烦地索取各种财物,败坏社会风俗。如果不对这些“奸徒”严惩,社会流弊不止,教化不正。他认为之前的律例对于“卖休”案件中的媒人的惩罚太轻,应该加大惩罚力度,这样才能使他们畏惧惩罚而不敢轻易“生拆活妻”,违背“礼义”。
以下这些“卖休”案件显示的情形与湖北按察使描述的有所不同。并不能看到“卖休”案件是受媒人挑唆,而多是卖主主动联系媒人,希望可以找到买主,或者并无媒人。身价银没有半入媒人手中,媒人也并未经常索要财物,很多媒人往往对“卖休”案件真实情形并不知情。我们先来分析“卖休”的缘由。
贫困
在笔者搜集的这些案例中,因贫困而休妻嫁卖的案件最为常见,110件刑科题本中有68件明确提到因贫“卖休”。尽管如前所述,妻子若无违犯“礼义”的行为,丈夫不能随意出妻,然而在社会实际中,因贫而“卖休”的行为还是经常发生。若是贫困可以将妻子休后嫁卖,以此获得一笔身价银,这亦显示了男子将妇女视为财产的心态。
同治八年(1869)正月间,刘其受因贫苦难度,向伊妻张氏商允,央陈习为媒,卖休与吕城溃为妻,议定财礼钱二千四百文,当即收清。[17]
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二十日,严氏先嫁给廖克先为妻,生有一女,同治年间廖克先因为穷困将妻子卖休与刘中发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十二千文,光绪三年(1877)刘中发又因夫妇不合,央求郭铁匠为媒,复将严氏卖休与素识之袁元振为妻,得钱三十千文。[18]
李氏系介休县人,先是嫁给本县人张四为妻,张四故去后,再嫁本县人杜铁柱子为妻。高永德向在介休县充当帮工,咸丰八年(1858)九月,杜铁柱的儿子因贫困难以度日,于是凭媒董正魁等说合,将李氏卖休给高永德为妻,钱十七千文,写立卖契。[19]
王树步,璧山县人,年三十二岁,父母俱故,没有弟兄。凭媒接娶陈氏为妻,素睦,没有嫌隙。同治五年(1866)八月,因贫难度,把陈氏卖休与徐桢俸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千五百文。[20]
凃玉美,年四十岁,慈利县人。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印氏先嫁向万彬为妻,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内,凃玉美在湖北地方闻向万彬因贫要将印氏卖休,就央向邦愿、向盛宝为媒。议定财礼钱四十四千文,买休印氏为妻,向万彬亲立婚书。[21]
清代政府和律例强调妇女应守节,婚姻应符合“礼义”,不过在贫困的现实面前,由于“礼义”并不能解决困境,为寻求生路逼不得已而休妻嫁卖的行为仍然较为普遍。这些案例最后的判决未有证据显示法律考虑到贫困的现实及妇女的处境,在判决时多严格比照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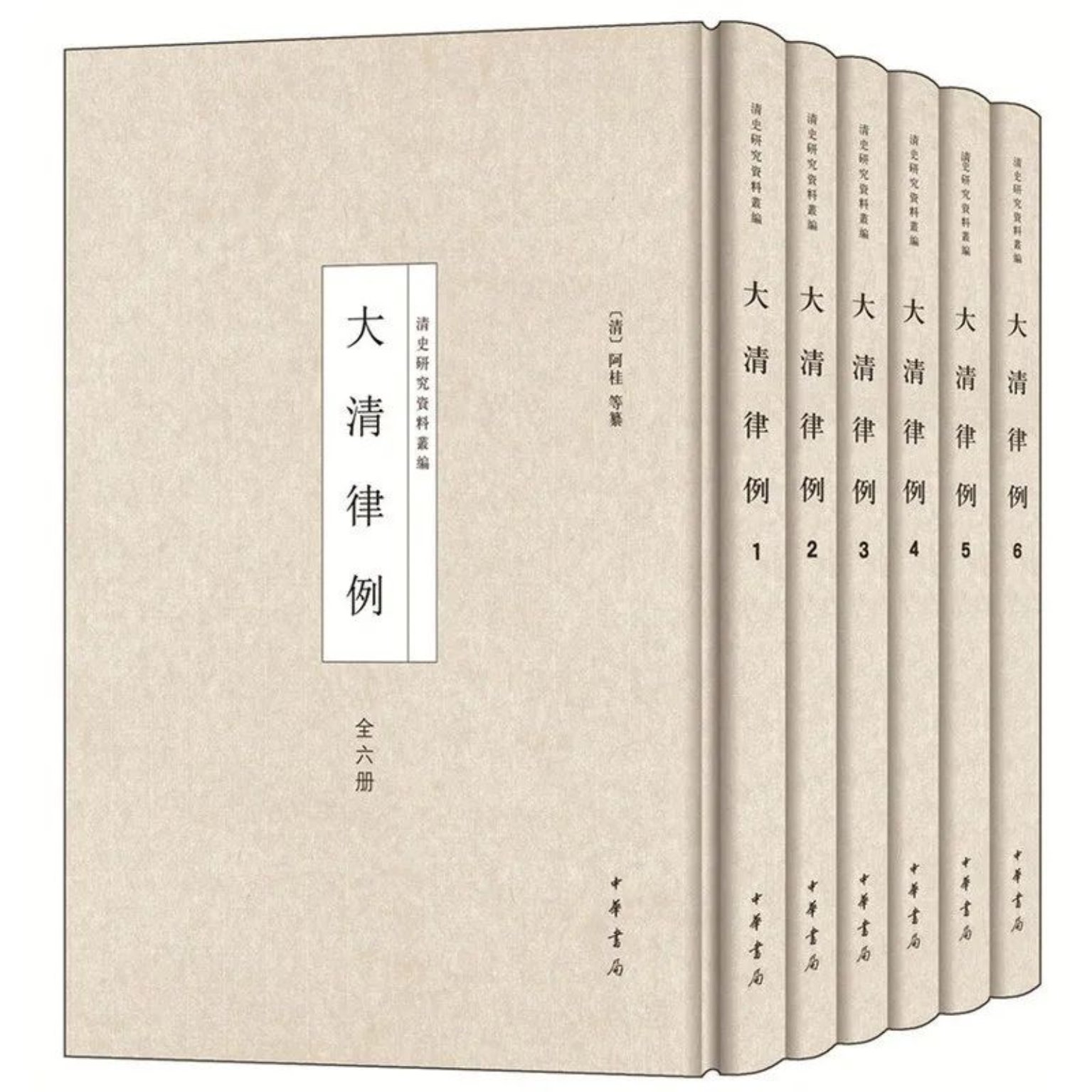
妇女通奸
清代法律鼓励妇女守节,要求妇女应该遵守“礼义”,妇女通奸的行为显然违犯法律和“礼义”,男子发现或怀疑妻子有通奸行为(嫌疑),可以选择休妻,而有的为贪图钱财,将妻子休后又将其嫁卖。还有一种情形是丈夫贪图钱财,纵容妻子与人通奸,随后又将妻子嫁卖给奸夫。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的案例中,有18件因为妻子(包括怀疑)通奸而“卖休”。
刘氏先是嫁给了程明德为妻,后来有一天程明德看到妻子与人戏谑,就怀疑她品德不端与人通奸,于是就在道光十三年(1833)把他卖给了曹彦为妻,曹彦因为妻子去世买了刘氏。后来刘氏又被库四等人抢去,卖给河南仝姓的一户作为妻子,道光十三年又转到萧县居住。[22]
孟书耕娶范滑氏前夫之女毕氏为妻,毕氏与范树椿通奸,范树椿用强逼弱写休字,复将其妻带去。范因通奸而恋奸,逼写休书,许给孟书耕盘费京钱二百吊。法律判决:“通奸罪止枷杖,惟该氏因奸致本夫休弃罪,殴彼写婚书,未便仅照和奸本律问拟,应照买休人与妇人用计逼勒本夫休弃律,杖六十,徒一年。犯奸之妇杖决徒赎给伊夫领回,听其去留。”[23]
咸丰九年(1859),城幅平与赵辛氏通奸,赵三才等知情贪利纵容,十年三月间赵三才因贪财将赵辛氏卖与城幅平为妻,身价钱二十千文,立契过门,并无媒证。[24]
然而无论如何,违犯“礼义”的妇女遭到丈夫休后嫁卖,终究显示了法律对妇女的限制以及丈夫在家庭中的强势。对于一个妇女而言,若违犯“礼义”而有“犯奸”的行为,则在法律实践中很难获得清代官员的同情和怜悯。
拐卖
还有一种情形是男子将妇女奸拐后,捏称夫妻并将其嫁卖,由于妇女违犯“礼义”,此种情况下法律实践中亦很难对其有多少实际保护。在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这类案件有8件。
杨淀前是四川巫山县人,至建始县地方佣工度日,曾在贺良经家寄住觅工,始与贺良经之女认识,贺长女幼字游家清为妻,尚未接娶成婚。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九日,贺良经与子贺家文均赴向泽槐家帮工。贺家文之妻黄氏令贺长女挑水做饭,长女畏冷不允被黄氏斥骂,气忿欲往外祖家投诉。行至中途因为积雪不知去路,正想返回去的时候,遇到了杨淀前。贺长女即把情实告诉了杨,杨起意要把长女诱卖,于是就把长女诱至县属林家岭僻静的地方,当时已经很晚,就令长女同进山洞歇宿行奸,长女这才意识到被拐,苦闹不依。杨这时威胁说如果不依,就用刀杀死她。长女被逼无奈,于是同宿成奸。次早杨认长女为夫妇同行,并且要求长女勿要向人说破已被奸污,长女也随口答应。
后来到了恩施县属大湾地方,杨捏称贫苦难度,欲卖伊妻。央求不知拐情素识的崔元宣代觅娶主,值刘明书的妻子故世,正拟续娶,崔元宣向刘明书的父亲刘文贵说合,议定身价银十五串,二百文。杨书立字据,将长女卖与刘明书为妻,得受身价逃走。刘文贵于是月十四日主令刘明书与长女成婚。长女未吐实情,维时贺良经与子贺家文回家,询悉贺长女因被黄氏斥骂外出未归。寻觅到彼,长女向贺良经等哭诉前情,刘文贵始知长女被杨所卖。
法律判决:“杨淀前除吓逼成奸罪不议外,合依诱拐妇女卖为妻妾,被诱之人若不知情者,为首者拟绞,绞监候。事犯在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恩诏以前,系在部议准之列,应准援免。再有犯加一等治罪,仍追身价银。”对于贺长女,则因为被逼奸已成,“不知情之娶主刘明书具领,贺长女被杨逼奸并甘心失节,应毋庸议”。[25]
妇女若与男子有奸,纵然是被男子拐卖,法律实践中考虑的仍是“礼义”,若妇女“甘心失节”,便很难获得清代官员的同情。在该案中,奸拐贺长女的杨淀前最终并未受到惩罚。相反,由于贺长女已失节,在一个重视“礼义”名节的时代,她的处境应较为艰难。
夫妻不能相安
对于夫妻不合的,也有男子将妻子休后并嫁卖,以此获得一笔钱财,这同样显示出社会实际中妇女的弱势地位。笔者搜集的案例中明确提到“不睦”或”不能相安”的案件有11件。
曾氏最初嫁给刘姓男子为妻,后刘姓丈夫死了改嫁给林义方为妻,因为夫妻“不能相安”,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的时候,符圣南向林义方议订财礼钱六千文,“知情买休为妻,和睦无怨”。[26]
宋氏为山东嘉祥县人,年二十九岁,父亲宋丑,别没亲属,从前嫁给同县人师温为妻,生有一女。师温因为与其不睦,同治元年(1862)把宋氏卖给任金方为妻,任金方知情。价钱四十千文,并没媒证婚书带同。[27]
疾病
男子有病因为无钱医治,将妻子休后嫁卖获得钱财。或者是妻子有病,男子无钱医治,将其休后嫁卖。然而嫁卖与否,主动权限都在丈夫。在笔者搜集的这些案例中,提到疾病往往是与“贫困”“不能养活”等并列的,这类案件与前述贫困有交叉的部分,明确提到因疾病而“卖休”的有9件。
沈宗富供称邹氏是其女人,素患痨病,不能养活,起意卖休,托素识的陈桂林为媒,道光十二年(1832)四月二十三日,说是其孀居弟媳,黄登照情愿承娶为妻,议明财礼钱五十六千文。沈宗富供:“小的实因贫卖休,非女人情愿,女人现在因病不能到案,是实据。”最后判“沈宗富因贫穷卖休,照卖休本夫杖一百律,应杖百。罪上减一等,应杖九十。邹氏讯非情愿卖休,且有痨病,应仍令沈宗富领回,免其离异”。[28]
这里法律考虑到邹氏在卖休案件中并非情愿,而且又有疾病,如果强制离异的话,邹氏难以生存,因此让其丈夫将其领回,不过这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实际上,对于身处贫困境遇中的底层民众而言,其行为选择十分有限。
同样,男子身处疾病中,因为无钱医治,会将妻子嫁卖获得钱财。宋氏先嫁给吴大盛为妻,后来吴大盛因为患病成废,同治元年(1862)就将宋氏卖休与李开扬为妻,得受财礼钱十千文。李开扬知情买娶,并无媒证。[29]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案件中,是否选择卖休,其主动权则在于丈夫,而不管妻子是否同意,这显示了“夫权”对家庭事务的支配。
需要强调的是,刑科题本中的“卖休”行为一般都是附带提及的,并且在法律判决时多作为“轻罪不议”,既然这些案件主要是作为命案上报的,那么卖休案件为何会引发命案?

身价银争执
在笔者所搜集的案件中,因身价银而起争执并引发命案的最为常见,在110件刑科题本中有62件。正如苏成捷所认为的那样,“卖妻与其说它斩断一个人与其妻的关系,不如说它启动了卖主与买主之间的一种崭新且持续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买主在道德上被视为有义务帮助卖主,因为卖主的不幸造就了他的利益。这种买主与卖主间的不平衡,也意味着到了公堂之上买主比起卖主更可能输掉诉讼。这就是为何在卖妻已经过了很久以后,买主有时候仍然支付卖主两次或者更多次找价的原因,而且这些找价数额相当高,偶尔甚至超过原来的买价”[30]。无论买主还是卖主,他们都显示出将妇女视为其财产的心态。他们对财产本身的关注要甚于对妇女境遇的关心。
李开扬知情买娶宋氏,并无媒证。牟以得与李开扬交好往来,见面不避。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不记日期,宋氏外出割草撞遇牟以得,牟与宋氏通奸。李开扬撞获,称欲送官,牟央求免送并许帮助钱米,李开扬贪利纵容。后来牟以得无力资助。李开扬常向以得索钱,每遇无钱付给就对宋氏殴骂,不许与牟以得往来。同治元年二月初三日,牟以得复至宋氏家中,李开扬当向牟借钱五百文,以得佯装回家取钱送给李开扬,李应允,各自出外赶集。牟屡次受李开扬勒索威逼,又没钱送给,定被断绝往来,起意将李开扬致死以便与宋氏长聚。当向宋氏商量,宋氏亦常被李开扬殴打谩骂,当即答应。在李开扬回家经过的僻静之处,牟以得在此静候,用刀扎颈后,李身死倒地。法律判决:牟以得除犯奸轻罪不议外,合依谋杀人造意者斩律拟斩监候,照例刺字。宋氏除犯奸并私埋为从轻罪不议外,合依谋杀人从而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杖一百,流三千。[31]
同治八年正月间刘其受因贫苦难度,将伊妻张氏卖休与吕城溃为妻。光绪元年刘其受因乏钱用度,起意重索。声称吕城溃欠伊卖休钱二千四百文,欲令补给。吕城溃斥责其不应重索,信口谩骂,刘其受回骂,吕城溃受伤身死。[32]
对于因贫困而“卖休”妻子的底层民众而言,其内心应是忿懑的。妻子才能过活,在婚姻关系交换中象征着贫困和无能,容易受到族人的指责。毕竟“卖休”行为是违犯“礼义”的事情,一个人为了钱财连妻子都可以休弃嫁卖,这在社会实际中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公开的事情。将妻子“卖休”,并不容易就此结束与妻子的关系,卖主容易将自己身处贫困境遇中的不满都转移到买主的身上,因此反复要求补给钱财。他认为自己的境遇没有因为将妻子嫁卖而有好转,
而买主的“落井下石”反倒加剧了他的悲催境遇。而买主的心态则与其相反。对于多数同样身处贫困处境的买主而言,支付身价银本身对他们而言就不是一笔小数目,卖主反复要求给付钱财,当然加剧了他们原本就很贫弱的处境。而且在他们看来,既然身价银已经议定交付,就不应该再与妇女有什么纠葛。因此在“卖休”之后,容易引起诸多诉讼和争执并造成命案。
妇女通奸
引发命案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妇女通奸,这种情形也是复杂多样的:妇女有可能在被“卖休”之前就已同买主通奸,其丈夫将妇女“卖休”给“奸夫”;妇女被卖休以后,与人通奸,因事发而引起争执。在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此类案件有31件。
宋氏供称其为山东嘉祥县人,年二十九岁,父亲宋丑,别无亲属。从前嫁给同县人师温为妻,生有一女。师温因为和其不睦,将宋氏卖给任金方为妻。之后和张保则同村居住,张保则和任金方往来,见面不避。咸丰九年(1859)八月间,任金方外出张保则与其通奸,后非一次,并没得过钱财。任金方并不知情。十二月二十二日,张保则人来被任金方撞破,张保则逃走。任金方把宋殴打,并说和张保则并不甘休。二十九日早,宋出外拾柴,遇见张保则,向他告知前情,张保则说不如把任金方谋死。宋应允。约定那夜下手,二更时分任金方在炕边熟睡时,宋开门等候张保则来,张保则来了之后,骑坐任金方身上用手摁住咽喉。任惊醒,手脚乱挣,宋随手拿刀扎任,张用力摁住任,当时毙命。最后,宋氏“依谋杀人从而加功拟绞监候”。[33]
李氏系介休县人,先是嫁给本县人张四为妻,张四故去后,再嫁本县人杜铁柱子为妻。高永德向在介休县充当帮工,咸丰八年九月,杜铁柱儿子凭媒董正魁等说合,将李氏卖休给高永德为妻,钱十七千文,写立卖契。李氏在卖休给高永德之前,两人就已通奸,被窥破奸情才被卖休。高永德的儿子高冬仔从来不叫她继母。并且曾劝高将李氏赶走。后双方发生口角,李氏被高冬仔殴伤身死。[34]
凃玉美买休印氏为妻,与印氏和好无嫌。郑启帼向与其认识时,常相往来,印氏也见面不避。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二十一日凃在外,回家看见印氏房门关闭,心疑探望,看到郑与印正在床上行奸。凃忿激,拾取木棍打斗进内喊捉,郑跑走,凃就用木棍连殴打印氏右肩,印氏撒泼哭喊,又用拳打伤她,印氏伤重,于二十三日身死。[35]
乾隆十年(1745)正月,长安县民定武用银十两,将李洪银妻子景氏聘娶为室。后来李洪银后悔,退还了七两银子,要求将景氏领回,但这时景氏已经怀孕。双方同意退还,条件是如果定武资助所生子女的食用,所生子女就归定武所有。景氏回去后,又被其夫李洪银纵奸张义德。一日定武去景氏家中看到景氏所戴首饰,以及屋内棉纱等,知道这是张义德所送,就斥责景氏,一气之下就将其夫妇二人杀死。[36]
由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弱势,即使是通奸行为,其中也显示不少是由丈夫逼迫或默许妻子与人通奸,以此获得钱财和资助。而对于那些妇女而言,如果违犯“礼义”有“犯奸“行为,便难以在法律实践中获得同情和保护。
与前夫(或后夫)的矛盾
那些被丈夫卖休的妇女,其内心可能容易充斥忿懑。毕竟丈夫为获得钱财而将其休后嫁卖,夫妻因“义”而合,如今既然已将其卖休,恩义和情感也就断绝,她们无法选择,只能同一个新的可能并不认识的贫困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且,那些被丈夫卖休的妇女在新的家庭中也可能同样身处贫困境遇中。这项与“通奸”的统计有交叉,若排除因通奸而引起矛盾的有13件。
王树步,璧山县人,年三十二岁。同治五年(1866)八月间因贫难度,把陈氏卖休与徐桢俸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千五百文。十一月初六日下午,陈氏来家说他纺有仔四两,没有带去,叫王清还。王斥说陈氏不该混索,陈氏乱骂,王回骂,陈氏顺手用木棒打王,后来被王打伤身死。王树步判“绞监候”,陈氏“听从卖休,罪有应得。业已身死,应毋庸议”。[37]法律判决中认为陈氏自愿被“卖休”,因为违背“礼义”而没有守贞,对其被卖休的境遇并不怜悯,认为其“听从卖休,罪有应得”。
法律在判决中着重考虑妇女是否违背“礼义”,而不会过多考虑妇女的处境。法律中的“礼义”对于妇女更多的是贞节限制以及“夫权”的支配。
并非所有妇女都同意丈夫的“卖休”行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实际中,妇女的反抗行为仍然有限。

自尽
身处此种环境之中的妇女选择有限制,如果不同意丈夫将其卖休,她们的反抗行为有可能就是选择自杀。
道光十年(1830),曹陈氏配与曹玉书为妻,成婚多年,曹私将陈氏凭媒王祥等卖休与王潮富。陈氏均不知情。陈氏感到无颜见人,自缢身死。[38]
对于陈氏而言,被丈夫卖休是一件玷污其名节令其羞愧的事情,在她看来,这会让其无颜见人,因此她选择自杀。笔者搜集的案例中提到自杀的有3件。
复仇
在这种为获得钱财而将妇女休后嫁卖的婚姻交换关系中,妇女选择有限。妇女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物品在流通,利用妇女的生育功能使贫苦底层男子的家族得以延续;或者男子纵容妻子与人通奸,以此获得钱财,之后再为钱财将妇女卖休给“奸夫”。然而,妇女终究不是物品,有的妇女会做出极端的行为:要么自杀,要么复仇。在笔者搜集的刑科题本中,提到妇女杀死前夫的案件有17件。
赵辛氏籍隶武陟县系赵三才之妻,赵三才并无生业,与城幅平素识无嫌,赵辛氏习见不避。咸丰九年(1859)十月,赵三才贪利纵容赵辛氏与城幅平通奸。十年三月间,赵三才因贪财将赵辛氏卖与城幅平为妻,身价钱二十千文,立契过门,并无媒证。后来赵三才将住房变卖,城幅平亦移居修武县开设饭铺生理。后城幅平因嫌赵辛氏懒惰,欲将该氏退还。十一年八月间赵三才路遇赵兴义,向其告知城幅平与赵辛氏通奸卖休情由。赵兴义以幅平奸买其族中妇人,心怀不甘,即同赵三才往向理论。赵三才因无住处,即托赵兴义代借李张氏喂牲口空屋家,希图多得身价银。赵辛氏不允,赵三才时常殴逼。(赵三才)声言(若)不愿,定即(将赵辛氏)处死。赵辛氏恨极,起意将赵三才致死,自寻生路。十月初一日,赵三才患吐泻病,神气昏迷。赵辛氏见赵三才熟睡,寻得一根麻绳,将赵三才勒死。赵辛氏除听从卖休并犯奸轻罪不论外,合依谋杀人斩监候律,拟斩监候。[39]
显然,复仇终究不可能改变其境遇,将前夫杀死当然不能寻得生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卖休”行为,显示出以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基本区分为原则:卖方出卖妇女的身体以获得钱财,买方利用妇女的生育功能延续其家族。
(三)妇女离婚:审判离婚中的“礼义”
滋贺秀三曾指出,与父子、兄弟关系相比,夫妻关系被认为是“人合”“义合”,即后天的、社会的结合,会因后天的理由而解除。并且他认为这样的例证和说法很多,比如《唐律疏议》中“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宋代陈振孙说“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矣”、清代钱大昕称“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40]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妇女依据其单方面的意思就可以要求离婚,法律实践中的离婚案件仍然着重考虑的是“礼义”和对“夫权”的重视。
因夫长期未归而离婚
法律实践中,丈夫在外长期未归,妇女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可能会要求改嫁。
王美纯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出外,五年未归,留下妻子李氏在家。有人作媒,将李氏嫁给了刘廷先,王美纯的哥哥王美常写的领字,并收了刘廷先九千钱。后来王美纯回来后发现妻子嫁给了刘廷先,于是告到官府,“小的今年冬月初四日回家,见妻子李氏不见,小的查问在刘廷先家,不知是刘廷先拐去?不知是哥子嫁卖?只求赏问哥子王美常就得明白”。王美常称弟媳确实嫁给了刘廷先,但并不是其嫁卖,而是因为自己不识字,只是听说叫人写了领就可以得到九千钱的盘缠。
县官正堂判词称该案由王美纯长期外出音讯全无而致,遗妻李氏在家,因为又赶上年岁饥馑,根本无法生存,李氏不得已才嫁给刘廷先。王美纯的兄长领取九千二百钱属实,并且根据王美纯的口供,亦可证实其妻李氏确属他人,“王美纯因年荒出外,弃妻不顾,而李氏不能守节令嫁,均非义夫节妇,刘廷先擅娶有夫之妻,亦属不合”。王美纯、刘廷先本应受到法律重究,但考虑到此事发生在灾年中,“姑念事在荒旱之年,从宽免究”。最后县官判决“断令刘廷先出钱十千给王美纯具领,其子亦令领回”。[41]
《大清律例》中规定:“期约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42]与刑科题本相比,地方诉讼档案显示出一定的适应性,不过这种适应性并不能违背律例本身的规定以及法律中的“礼义”。在该县官看来,王美纯因为荒年而外出五年,留下妻子一个人在家,“弃妻不顾”,这不是一个“义夫”所应行之举;而李氏不能守节而改嫁,同样违背“礼义”贞节,也不是“节妇”所应行之事。既然夫妻双方皆未遵守“礼义”,那么县衙就可以考虑现实情形:王美纯已经五年音讯全无,这基本上已经达到律例中关于此类情形规定的时间上限,加上又是灾荒之年,王美纯的兄长作为家长也领取了财礼钱,因此县衙承认李氏再嫁的事实。但是县官同时又要求后夫出钱十千,其子领回。这既是安慰其前夫,不过亦表明县衙要更倾向于照顾前夫的权益。
类似的情形还比如丈夫失踪多年未回,妇女又与夫家家长难以相处,所以主动向官府请求由其父母领回择户另嫁。巴县档案中有一例,咸丰三年(1853)五月,刘二姑因为丈夫长期未归,请求县衙判令由父亲刘和祥将其领回另嫁他人。
刘二姑供:“今年十六岁,父亲刘祥和自幼把小女子抱与这王命用神的孙子王绪儿为媳,尚未完配。道光二十八年冬月间,公公命用神将小女子的翁王大猷并王绪儿逐出未归。今年五月间公公屡次嫌贱小女子,才来案下鸣冤的。因王绪儿逐出多年未回,断令父亲刘祥和把小女子领回择户另嫁就是作主了。”[43]
刘二姑在向县衙的供词中,首先强调不是丈夫未归,而是自己被公公嫌贱,这样自己就并非不能守节而违反“礼义”,最后县衙堂批“刘祥和遵谕将二姑领回另嫁”[44]。

妇女与翁、姑矛盾
在家庭关系中,矛盾的焦点往往不是夫妻关系,而是媳妇与翁、姑之间的矛盾。如果丈夫站在父母一边,那么妇女就更容易处于弱势。矛盾如果尖锐的话,妇女的家人可以要求将其领回另嫁;或者男方的父母要求其与妇女结束婚姻关系,让妇女的家长将其领回。县衙对此案件的审理往往并不强加干预,咸丰朝巴县衙门档案中有几例:
郭氏的父亲郭永吉要求领回他的女儿并另行改嫁,因为郭永吉认为女儿郭氏与刘欲泰成婚三年来,一直与刘欲泰的母亲有矛盾,争吵不断,郭永吉担心这样下去会容易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郭永吉要求把女儿郭氏领回,重新改嫁。[45]
朱万美向县衙诉称要求儿媳朱彭氏应被她父亲彭万有领回,另行择户改嫁,并且要永远与他的儿子朱元盛断绝来往。原因在于他认为儿媳过于泼悍,从来都不料理家务,如果训斥她的话,还动不动就要自缢跳河,实在无法忍受。他认为儿媳如此行为也是受到她父亲彭万有的挑唆。因此要求彭万有将其女儿领回,与其子朱元盛离异并且断绝往来。[46]
妇女因与翁、姑矛盾而离婚的案件中,男方仍是主导,极少有妇女因此主动要求离婚的,法律实践中,县衙也不能直接越过男方的名义而直接判决离婚。
夫妻失合
这类案件往往最为复杂。夫妻失合,如果两厢愿离,法律对此也承认,不过这类案件极少有妇女主动要求离婚的。丈夫主动要求离婚的,则会突出或夸张妇女的行为如何“泼悍”;妇女及其家人则可以要求男方返还出嫁时所收物品,以及突出自己在家中遭受男方的暴力等,以此获得县官的同情。这些案件多是当事人的叙述,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鉴别基本事实。
妇女尽管很少因夫妻失合无法相处而主动离婚,但若丈夫希望结束婚姻关系,妇女可以要求男方返还出嫁时金银衣饰等,妇女若无明显违背“礼义”的行为,县衙也不能判决强制离异。因此妇女有时反倒可以利用县衙希望结案的心理,从而获得对其有利的判决。
徐以仁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川娶秦氏之女为妻,后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内搬回家乡楚地,“夫室参商控案,麻邑县主具准差行唤,中有王步街两劝说合”。秦氏考虑到“恩情义绝,务要以仁得秦氏嫁时金银衣饰等项,照单亲还。秦氏方免干休,将案息销”,其夫徐以仁“凭中自愿还出,比时凭中照单算明衣饰金银等项,共该银二百四十两正,凭中限至五月二十八日将认银还给秦氏亲收”。秦氏则“认限约收银,凭中还给以仁夫室,以免参商”。并且考虑到秦氏“日后永无异端,其立限约,此系以仁心甘情愿,并无中证勒逼等语。空口无凭,立出自认限约给与秦氏名下为据”,徐以仁以及四位凭中人的签字。[47]
不过多数情况下,妇女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田仕仁诉称自己将女儿嫁给表侄刘醇孝后,后者仗着他父亲遗留的财富,一直嚣张跋扈,经常欺凌自己的女儿,其女儿已经生了两子四女,但是刘仍然娶妾在家,并且视妻子田氏如仇敌,“不时拳殴脚踢,生以理劝戒,奈伊宠妾心坚,云生女与伊妾口角等语”。等到自己前去的时候,发现刘醇孝已经把女儿“打昏在地,不能言语”。田仕仁同他理论,不想刘醇孝更加凶狠。田无奈而隐忍回家,找到刘的兄长刘文衡说理,文衡则说“醇孝五伦已绝,不能管束”。没想到刘醇孝知此,更加凶横并且报复,还用刀把自己戳伤,因此将此禀告县衙。[48]
当然,可以说妇女家长为将女儿领回另嫁,夸张其如何遭遇不公。然而,在该案中县令可以查问证人(刘文衡),妇女的家长又有被女婿扎伤的实情,相信为将女儿领回亦不必将自己扎伤,相信妇女在家庭中居于弱势的应为事实。
在以下两个案件中,就可以看到男子为与妻子离婚,其在向县衙的供述中,如何突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泼悍”而无法忍受。
乾隆五十三年(1788),吴泰来诉称由于其妻子张氏没有生育,自己于是就花了三十六千钱买了沈泉发的婢女春梅为妾,数年中妻妾都非常和睦,但今年春梅突然变得泼悍,张氏理斥,反被春梅用洗衣棒打落了两颗牙齿,并且咬伤了右手指。对此,吴称其并未深究。没想到二十四日竟然收拾衣饰逃跑,后来在沈泉发的亲戚汪珍家找到。吴泰来认为春梅数年都很正常,妻妾相处正常,如今性情大变,是因为汪珍刁唆。如今竟然“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没想到汪珍害怕被指控,“是日沈泉发以嫌殴逃归事控案”。[49]
此案殊为可疑,照常情而言,春梅作为妾又是婢女出身,既然数年之中都相安无事,为何突然性情突然大变,这并不符合常情。吴泰来又称对方捏控,但又并未指出对方捏控的目的。事实上县衙对此也颇为怀疑,认为应先查明事实,县官怀疑是春梅在家中遭受虐待殴打而逃走。
同样,熊开宗为与妾周氏解除关系,则突出周氏如何“泼悍”,违背“礼义”而“不知妇道”,由此希望获得县衙的同情可以解除婚姻。
熊开宗诉县衙要求与妾解除婚姻关系,他称自己由于原配韦氏疯瘫,而父母年迈无人照顾,因此凭媒人娶故人孀妻周氏为妾,没想到这周氏虫蝎心肠,“不知妇道,非但不服使令,更敢悖逆翁姑。希望奉侍怡亲,谁料益增亲怒,悖亲罪恶,蚁咎何辞”。因此他认为“此种悍妇,七出已干。情愿凭官出退,以安家业,以顺亲怀,为此上呈”。[50]
巴县档案中,这些案件多由丈夫主动提起,妇女很少因夫妻失合而要求离婚。
妇女通奸
妇女因为违背“礼义”与人通奸而离婚的案件较为常见,如果男方因此要求离婚,往往最为容易。法律要求妇女守贞,妇女违背“礼义”与人通奸,不仅难以获得县官的同情,而且还可能受到县衙的惩罚。咸丰朝巴县中有数件涉及妇女通奸而另嫁的案件:
汪廷英的女儿汪氏因为和夫家的雇工陈二通奸怀孕,被夫家人撞破,告到官府,县衙判双方离异,并要求汪氏的父亲汪廷英领回女儿,择户另行改嫁。[51]
杨启普的妻子何氏与杨的无服杨光程通奸,后被杨启普发现。杨启普无法忍受,向县衙诉称要求与何氏离异。但是在族人的调解之下,杨启普撤回诉讼,考虑到何氏已经为其生育,最后没有选择离异,“奸夫”杨光程则要受枷示众。[52]
该案中,因为考虑到何氏因为已生一子,出于对家庭的考虑,在族人的调解下,杨启普最终没有选择离异,县衙也尊重其选择,不过“奸夫”则要遭到惩罚。在这一类案件中,清代县衙不能绕过丈夫而直接判决。
丈夫逼奸
对于妇女而言,如果遭受丈夫(或丈夫家人)逼奸而要求离异,最容易获得县衙的同意和怜悯。一般对此类案件,县衙会判决离婚。在重视妇女贞节的社会情境中,妇女可以凭此获得保护。
蒋老六是李氏的公公,但蒋老六却逼迫儿媳卖奸,此事被状告后,县衙要求李氏与蒋老六的儿子离异。[53]
刘何氏被丈夫刘仕义逼奸,刘氏不甘失节,因此向县衙请求与其离异,并且要求刘仕义返还衣饰和财银等。[54]
李幺姑被丈夫逼奸,李的母亲李禹氏要求将女儿领回。李禹氏供:“么女自幼凭媒许陈开材为妻,殊开材不务正业,屡次逼女儿李么姑卖娼。去年冬月间小妇人把陈开材具控在案休,恩审讯小妇人把女儿领回另行择配。”[55]
依据这些案件,可以推测前面讨论的“典妻”“卖休”等案件,妇女在家庭中因为贫困而犯奸,往往并非其情愿,相信其中不少是遭受丈夫的逼迫。只不过一些妇女坚决不从而与丈夫结束婚姻关系。然而无论如何,从这类案件中都可以看到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的境遇。
对于一部分民众而言,“礼义”对他们而言或许有另外的含义,那就是可以利用“礼义”而为其寻求利益。尽管清代法律实践中强调“礼义”,但我们不必夸大清代的“礼义”理念对底层民众观念的影响。然而,妇女在这些案件中不过是作为“财物”流动。

乾隆三十一年(1766),高朝位向县衙状告周之敏募卖妇女,高朝位称其侄女五姑嫁给沈朝统为妻,“所生一子年未甫周”。去年沈朝统因谭洪泽家遭盗窃一案而牵连入狱,“差拘押笼月余未审”,但后来有人来说沈朝统已死在狱里。考虑到侄女“衣食无措”,因此就在正月十四日的时候把她接到家里。几天后,到了正月二十一日,沈朝统的姨父周之敏来到家中说是要接侄女回去,并置办了酒宴请侄女,侄女跟去后,但是数日都没回来,去找周之敏问清情况,周刚开始是支支吾吾,后来索性避而不见。
高朝位称自己经过细访,原来是周之敏串通媒人将侄女募卖给谭洪泽的舅舅傅二(傅大德)为妻,“蚁闻骇异,前月二十三日蚁来恩辕,又知朝统十九日方遂毙命。似此恶棍,不惟套接募卖大干法纪,更胆生妻活拆,律理奚容?”因此乞求县衙“剪恶除奸”,使生者不致遭卖,死者不致含冤,将“永颂鸿庥不朽,伏乞太爷台前施行”。高朝位的叙述是如此值得怜悯和同情,他的行为都是为了考虑别人,考虑到侄女的境遇,自己还将其接到家中。然而所谓“无利不起早”,县官审讯查明的事实与高朝位所述并不一致:高朝位图借不遂,具告到县,庭讯之下,高氏仍配大德为婚。大德并未出有财礼。高朝位口口声声说的为“生者不致遭卖,死者不致含冤”“剪恶除奸”等不过是为了获得一笔财礼银,因为傅大德并未给其财礼银,高朝位才使用一套“礼义”说辞称侄女高氏被卖,说到底亦是为了将侄女嫁卖而获得身价银。因此,县衙判令大德缴银八两给沈朝统追荐费,并要求高朝位“不许滋事,甘结立案”。[56]
注释:
[1][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68页。
[2][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71—472页。
[3][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69页。
[4]题为“四川重庆镇总兵张士庆奏为严查奸蛮典雇妇女为娼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01-0010-034。
[5]《清高宗实录》,第三卷,“雍正十三年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1页。
[6]从中高层官僚的角度分析清代“教养”政治的,可参阅[美]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李兴华、胡玲等译,赵刚、孔祥文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7](清)全士潮、张道源等纂辑:《驳案汇编·续编》,何勤华等点校,第686页。
[8]《乾隆三十年七月三日巴县详报戴氏自缢一案申册为报明事》,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9]《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直里四甲四甲乡约张洪道复状为遵批实复事》,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90页。
[10]《乾隆五十九年刑房审单》,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89页。
[11]题为《报宁波府勤县人施淦友殴伤典妻庄应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113-016。
[12]题为“会审浙江钱塘县民金潮福因索讨典钱文起衅戳伤徐玉燕身死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1106-008。
[13]题为“报丽水县民江云生典妻索银致争砍伤叶锡其身死移尸毁尸灭迹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238-015。
[14][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85页。
[15]题为“报沅陵县民颜恭钲卖休妻事口角致戳伤颜恭钲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84-012。
[16]题为“湖北按察使德文奏为请严卖休买休惯媒设局哄诱之罪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01-0199-038。
[17]题为“四川资州仁寿县刘其受贫将妻张氏卖休起衅殴伤吕城溃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981-017。
[18]题为“报万安县民妇严氏致伤知情买休之夫袁元振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214-018。
[19]题为“报文水县人高冬仔杀死伊父奸卖休之妇李氏拟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6-010。
[20]题为“报重庆府璧山县民王树步殴伤卖休妻陈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68-002。
[21]题为“湖南慈利县民凃玉美踢伤卖休妻印氏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7-001。
[22]题为“江苏砀山县民曹彦被抢买休之妻刘氏一案四个月疏防限满抢犯无获开揭疏防武职各职名题参一案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2-2765-016。
[23]题为“审拟镶黄旗汉军世袭佐领范树椿买休人妻事”,录副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3996-016。
[24]题为“河南怀庆府武渉县民妇辛氏勒谋卖休之夫赵三才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32-005。
[25]题为“湖北武昌府建始县客民杨淀前吓逼贺长女成奸卖与刘明书为妻得财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012-012。
[26]题为“会审湖南益阳县民符圣南因知情买休并地界纠纷殴毙曾氏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13028-030。
[27]题为“报开封府张保则与宋氏通奸商同谋杀卖休本夫任金方身死该犯在监病故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10。
[28]题为“报罗山县民陈桂林卖休妻事起衅追殴黄登照跌殴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5-006。
[29]题为“四川绥定府东乡县人牟以得商同奸妇宋氏谋杀卖休本夫李开扬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09。
[30][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72页。
[31]题为“四川绥定府东乡县人牟以得商同奸妇宋氏谋杀卖休本夫李开扬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09。
[32]题为“四川资州仁寿县刘其受贫将妻张氏卖休起衅殴伤吕城溃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981-017。
[33]题为“报开封府张保则与宋氏通奸商同谋杀卖休本夫任金方身死该犯在监病故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10。
[34]题为“报太原府文水县人高冬仔杀死伊父奸卖休之妇李氏拟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6-0103。
[35]题为“湖南慈利县民凃玉美踢伤卖休妻印氏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7-001。
[36]题为“报长安县人定武买休景氏起衅杀死李洪银夫妇拟斩立决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0303-011。
[37]题为“报重庆府璧山县民王树步殴伤卖休妻陈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68-002。
[38]题为“报宿州民王潮富听从抢娶卖休之陈氏致氏自缢拟杖徒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43-004。
[39]题为“河南怀庆府武陟县民妇辛氏勒谋卖休之夫赵三才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32-005。
[40][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86页。
[41]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88页。
[42]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453页。
[43]《巴县县衙为王君海被控将孙逐出未归屡次嫌贱未配孙媳案录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63页。
[44]《刘祥和为遵谕将二姑领回另嫁事领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662页。
[45]《郭永吉为领回郭氏择户改嫁事领约》,《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306页。
[46]《朱万美为朱彭氏仍归彭万有领回另行择户与朱元盛断绝往来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100页。
[47]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1页。
[48]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1—192页。[49]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2页。
[50]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3页。
[51]《汪廷英为领回汪氏择户另嫁事领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42页。
[52]《杨光程杨光荣等为杨启普甘与何氏离异杨光程受枷示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432页。
[53]《蒋老六等为将蒋李氏逼娼被责惩日后不得翻控滋祸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113页。
[54]《为甘与刘仕义离异并将衣饰及女择配之日取有财礼银两均分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181页。
[55]《巴县县衙为李禹氏告陈开材等藐断歧控案录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733页。
[56]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89页。
——选自《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赵刘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 作者简介------------------------------------------------
赵刘洋,男,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黄宗智(UCLA 荣休教授)。现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研究成员,同时担任复旦大学任重书院导师、复旦大学望道导师。主要学术兴趣:法律社会学、海外中共学、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史。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围绕妇女、婚姻、家庭展开的法律社会史著作。书中以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为视角,对与妇女权利直接相关的法律实践做了细致梳理。通过深挖诉讼档案,作者对清代、民国、1949年至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离婚案件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剖析,还原了大量关于妇女离异、典妻、审判诉讼等历史细节,揭示了近世以来相关法律制度与诉讼实践在妇女权利的保护或损害等方面远为复杂的非线性悖论关系。全书吸收了大量中外学者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权威成果,并尝试与重要的学术观点对话,表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并融合了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妇女史、法制史研究的探索上做了有益尝试。
☆目 录--------------------------------------------------------
导论海外学术界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方法论反思/1
一、引言/1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社会基础:东方社会理论的反思/4
三、帝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功能:马克斯
影响/20
四、小结/36
第一章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家庭: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妇女自杀为例/40
一、“滞后道德”的法律实践与妇女自杀/41
二、“超前道德”的法律实践与妇女自杀/58
三、小结/72
第二章清代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75
一、清代关于“离异”的法律/75
二、从妇女张氏之死看清代妇女的生存境遇/85
三、清代法律实践中的“离异”妇女/99
四、小结/134
第三章民国时期的妇女离婚诉讼/136
一、民国法律的变化/136
二、法律实践中的离婚妇女/143
三、法律实践中的妇女权利困境/154
四、小结/161
第四章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163
一、引言/163
二、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则/165
三、政治动员中的婚姻自主/169
四、婚姻自主与社会实际的矛盾/172
五、婚姻自由与离婚判决依据/176
六、当婚姻自由遭遇生存伦理/179
七、法官如何确定离婚判决依据/181
八、小结/198
第五章 中国婚姻“私人领域化”? ——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200
一、现有的分析/201
二、当代中国婚姻法律条文中的实用规定与道德原则/207
三、当代中国法律诉讼实践中的妇女离婚/217
四、在诉讼案件之外:实质主义道德理念与妇女权利/231
五、小结/234
第六章财产权利与家庭政治:当代中国离婚法律实践中的房产分割/237
一、引言/237
二、权利观念与婚姻家庭/238
三、夫妻房产分割争议的类别/243
四、家庭正义观念/255
五、“折价款”与家庭政治/258
六、法律对弱者的保护与家庭政治/262
七、小结/266
结语/268
参考文献/274
☆名家推荐-------------------------------------------------------
赵刘洋的新作跳出了目前仍然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研究陷阱,即要么简单凭借现代西方的个人权利法理,要么简单仅从中国的传统或仁治理念,来评析中国清代以来到当代关于妇女的法律体系。通过近距离地检视中国清代以来的离婚法律实践,赵刘洋的详细研究展示的首先是条文与实践双维中的复杂关联、张力和互动,清代如此,近、现、当代也如此。整个体系,尤其是关乎性别权利的法律,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充满张力的继续演变过程之中。对妇女的公平待遇的追求尚有待在实际运作和法律条文中逐步澄清和概括。
——黄宗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
不同于革命史观下对妇女解放的高歌,亦有别于一般性别史研究在高扬极端女性主义大旗之时,又把其所声讨的受父权制约束而撰写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妇女史,转换成包括上层、下层在内的中国女性自由主义的浪漫史,赵刘洋的新著通过对清代、民国乃至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离婚案件细致而深刻的剖析,向读者揭示了近世以来相关法律制度与诉讼实践在妇女权利的保护或损害等方面远为复杂的非线性悖论关系,是为中国妇女史、法制史研究难能可贵的新探索。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在从清代到民国再到当代的长时段变迁中,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制度规定及其司法实践是最能体现古今中西之张力的具体领域之一。我们在其中既可看到大量明显的断裂之处,又能够感受到存在着另一些同样明显的延续性。《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一书借助丰富的案例,生动展示了此方面中国法律实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版图中,法律史无疑是边缘角色,但历史一再表明,颠覆性的革命力量往往发端于边缘——在本书中,赵刘洋博士就展示出了法律史研究特有的力量。在这里,房产是但不只是物权法上的物,婚姻是但也不只是家庭法所调控的关系,女性是但更不只是拥有物、结成婚姻关系的行为能力人,所有的法律概念,都镶嵌在社会中,形成于不断变动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面向社会秩序的整全性视角,连接过去和当下的纵深历史观,成就了本书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在黄宗智先生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历史社会法学的研究中,霍姆斯意义上的作为法律生命的“经验”才得到重新发现,并且扎根在中国大地上。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辑推荐--------------------------------------------------------
清代“离异”妇女的生存境遇如何?民国时期妇女权利在法律实践中面临怎样的困境?改革开放前法官如何确定离婚判决依据?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房产分割有着怎样的特点?近300年有关妇女、家庭与法律地位的社会史,通过本书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是一本很容易引起时代共鸣的书。虽然作者关注的是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但“离婚”“离异妇女”“离婚诉讼”“房产分割”这些日常生活中频频接触的词语,却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时产生时空错位的感觉。书中“从妇女张氏之死看清代妇女的生存境遇”一节,更是让人容易想到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名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从书中摘引的与妇女张氏之死一案直接相关的买主(崔二珩)、张氏前夫(闫洪廷)、夫家家长(闫起盛)、张氏之父(张世珍)、媒人(王张氏)的审讯记录,以及县衙的判词,大历史背后一个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张氏的悲惨处境催人泪下。
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对妇女的公平待遇的追求道路上,法律做出的尝试与实践。
|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