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五讲在线上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兼任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宋代城市研究的几点体会”的学术报告,历史学院以及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近百位师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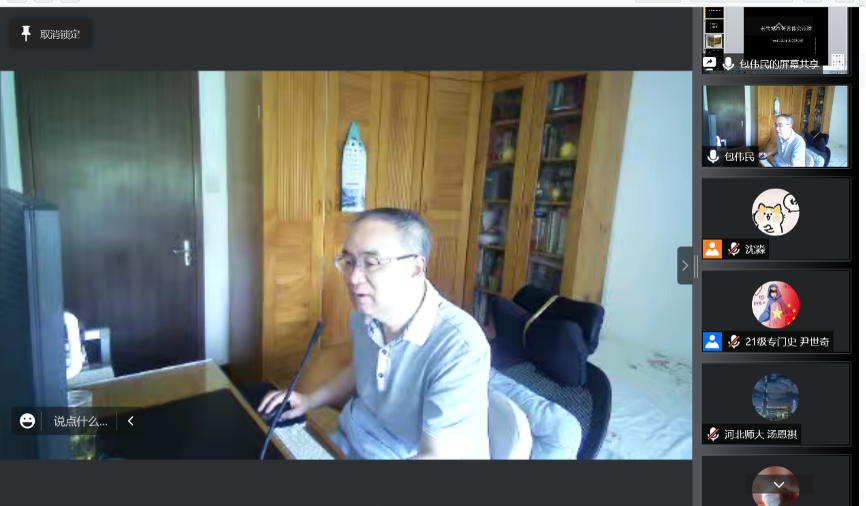
宋史素来是中国古史研究的显学重镇,而宋代城市研究因关涉领域既广,拓展空间又富于层次,更是宋史学家着力探讨的重要议题。在本次的讲座中,包伟民老师在其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市民” “市民文化” “坊市之变”等几个方面,对宋代城市研究中所遇到的史料研读、范式构建、史实重构等内容展开分析。
包老师首先以理论如何“祛魅”开篇,认为史学研究理论是人们经过分析与归纳所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些结论,其需求可归纳为三方面原因:一是基于历史某些共性的相互参考;二是基于历史复杂性的路径借鉴;三是基于史实复原难度的研究需要。包老师强调,理论在分析过程中“引导”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一旦被人为披上神秘的外衣,就常常对史学研究造成复杂的影响,观察视角、涉及层面、分析方式的不同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论。学界往往会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区分,前者为“史观”,带有些许信仰的意味,多属于“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后者多指中观或微观层,涉及相对具体的结论,划属“可以讨论”范围。
在包老师看来,宋代城市史研究中所涉及内容,即属于“可以讨论”的具体结论,从这一角度出发,相关的理论都可以被视作历史研究的工具或方法。作为宋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领域、基础性议题,以此为例,对于厘清史学理论在宋史研究中的角色问题有重要指导作用。
包老师从“究竟何为市民”出发,首先讨论“市民”这一唐宋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他指出,史料中多以“市人”指称城市居民,但是当“市民”一词被用来翻译citizens这个名词后,中国古代“城市居民”与“市民”的内涵差异随之突显。过往的学人从城市居民群体类别属性展开讨论并形成了一些共识,即基于城市中的“官与民”或“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阶层分殊,中国传统时期的“市民”与西方文艺复兴语境下市民阶层,不应相提并论;与之相应,城市居民群体是否具有共性“文化”,是否必然地共享反封建、追求自由的心理属性,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然而,包老师进一步指出,即便如此,人们在论述过程中仍然离不开对欧洲市民文化的参照,认为这样的市民文化具有 “自由”“新型”的特质,以致此前论者划定的中西“市民”之间的性质差异,以及被小心剔除的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欧洲市民文化特征,其核心部分又被悄悄地请了回来。包老师认为,这与其说是对史实的归纳,还不如说是出于对某种历史演变进程的信念。
“市民”身份的形成和界定问题,引出了关于城居者 “文化”的讨论。随着城市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集聚,文人士大夫阶层纷纷迁居城市,城市作为由士大夫所主导的文化中心地位更趋加强,两宋时期显然延续了前代的城市性格而未曾发生明显转折。所以,在城市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媚雅”才是关键。包老师以详实的史料与当下现实相映证,得出如下重要结论:“宋元而下直至当今的社会现实,可以给我们以相当直观的启示,(城市文化)在清雅与市俗之间从来都存在着一种主从关系。”
宋代城市史中的“坊市问题”及其相关的范式构建是此次讲座的重中之重。包老师首先阐明了“范式”一词的概念和特点,指出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体系、理论框架,特点不外乎公认性定律、理论等构成的整体,为研究者所提供的可借鉴的研究纲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宋代城市史是宋史研究中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域,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基本理念和研究传统,同时也形成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新路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加藤繁的“发展范式”,及由该范式引申出的宋代城市“增长(发展)极限” 之说。
包老师认为,借助范式指导,既有的经典研究成果阐述了城区中的“溢出”与“撑满”现象。不过,此种城市规划格局中的“溢出”现象,一般只发生在城关附近的部分地区;而此种“溢出”现象的存在,也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城区的“撑满”与都市化。因此,如果具有反思“范式”的自觉,就可以期待摆脱对权威的迷信和自囿,在研究过程中检验成法,查勘成说,追求新知。
由此,包老师从“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入手,对宋代城市史研究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加藤范式”进行剖析,并对施坚雅、伊懋可、张泽咸、宁欣等多位著名学者研究成果予以对照讨论,重点落在所谓坊市分隔、封闭式城市制度崩溃等问题之上,进而提出一系列质疑,诸如“以规划性大都市为依据归纳得出的所谓从坊市制走向街市制之说,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宋代是否真的发生过一场包括都市革命在内的中世纪经济革命,使得城市在整体上从封闭走向了开放”等,并逐一予以解答。
包老师认为,加藤范式所讨论的坊市崩溃论,在史实层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究其根源则在于论者混淆了坊市制与坊墙这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我国城市起源的历史悠久,直接影响后世的“坊市制度”,该制度大致经历了“曹魏邺城—-北魏平城—-隋唐长安”的发展历程。而“坊”字本义通防,指的是四周筑有围墙的封闭区域。北魏沿用秦汉的“里”制,以“坊”代“里”,力图加强对城郭人口的管理。可见坊市制是城市管理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坊墙则起到了强制监督和人口隔离的作用,一般仅出现在大型都市,并不具备普遍性。包老师强调,今人因受加藤范式影响,以“规范”坊市分离的思路来解读考古资料,有时不免造成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之间明显的“自振激荡”的现象。
事实上,坊与市的分离更像是中国城市自然发展的结果,而非是精心安排的制度设计。包老师提出:在城郭聚落自然发展出的区位布局前提下,商贾、匠作虽然日益融汇于城市生活,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以群分、自成一区的基本格局却改变很慢。这种分离不仅体现在地理区块上,也体现在民众的身份限制上,这就是与坊市分离相应的市籍准入制度。城郭以防御作为它的基本功能,政府制章定例区分不同人群,加强对流动人口集中的市场区管理,顺理成章。这又在一定程度加强了居民区(里、坊)与市相隔离趋势。当然,市籍制又是政府向商贾征发赋税的制度基础,具有双重功能,现在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包老师又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范例,进一步指出由个别推论一般可能造成史学研究中的片面与失真问题。例如,从城市规模扩大、日常消费品实际购买辐射、市籍制衰落、税收变革等方面,推论出专制政府通过设计坊市分离制度 “控制”工商业发展,恐怕是今人从近世的立场出发对历史的误读。唐宋之间的城市史并不存在从坊市制走向街市制的过程,以少数规划性大都市的事例来归纳唐宋之间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实不可行。当然,对史实重构的可能性,包老师还是谨慎地予以肯定,认为应对研究资料残缺不全的困难,是史家无法逃避的功课。但也正是如此,史学研究必然是一个史事重构与现象解释(概念演绎)并重的过程,这也是评判学术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尺。
讲座最后,包伟民教授进行了收束和归纳:
首先,历史的变化与断裂总是局部的,延续才是主要面相。目前广泛被认可的观点,即从唐代以前“封闭”的坊市分离制,随着坊墙的倒塌,坊制崩溃,从宋代起进入所谓“开放”街市制这种说法,是在过于强化的“发展”范式影响下的一种虚像,而历史真实的演进比这种范式化的简单归纳要复杂得多。
其次,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任何试图简化而不能兼顾其他的说法都是危险的。唐宋城市市场形制的演变过程,与其说前后断裂,不如说延续性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缓慢的进步是历史演变的基调。
再者,从方法论层面来归纳,切忌简单、线性的观察思路,全面、综合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历史学强调全面地观察某一特定时期的人类社会,而不是像社会学那样,将人类社会分解开来,仅仅从各不同的侧面来做观察。历史认知之路需要更加全面而综合,兼顾历史的连续与断裂。
与会师生对包老师的讲座反响热烈,就唐宋对经济的控制问题、意向研究对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城市傲态”等问题与包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撰稿人:魏晋 尹世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