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2022春季学期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在线上举行。台湾大学历史系杨肃献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启蒙运动诠释的新视角”的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夏明方教授、杜宣莹博士分别担任主持人、与谈人。

讲座伊始,杨肃献老师从身处启蒙运动之中的哲人对该时代思想变动的两种考察方式谈起。他指出,一种考察方式是将启蒙运动视为“现象”,代表人物有法国启蒙哲士、百科全书编者达朗贝尔(D’Alembert)。达朗贝尔在其时代的思想脉动中,观察到一些思想“现象”——“新哲学思维方法的发现和应用,各种发现带来的知识热情,宇宙奇观在吾人内心激起的观念的鼓舞,都带来一种活跃的心智扰动”。另一种考察方式则将启蒙运动视为一个“过程”,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一种人们追求“理性自主”的“过程”:“启蒙是指人从其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解脱出来。”以上两种视角,均对后世影响深远。
接着,杨肃献老师转向后世史家对启蒙运动的诠释,并从研究途径的变动展开分析。杨老师指出,1960年代以前,启蒙运动研究的取径偏向纯粹“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重视分析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主要研究上层哲士(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霍尔巴哈和孔多塞等)及其经典著作。代表性研究有1930年代卡西勒(Ernst Cassirer)所著《启蒙运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此类纯观念史研究也有局限。杨老师指出,启蒙时代的哲士们并非一群在学院内从事“为知识而知识”探索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而是有其实际、入世的目标——改变社会。当代史家托马斯·芒克(Thomas Munck)也强调启蒙运动并非仅是欧洲文化精英的知识消遣活动,更是平凡大众的价值与信仰解放的真实过程。如仅仅局限在观念史的领域之内,无论如何深入,都无法揭示启蒙运动的真实意义。
鉴于此种考量,亦因年鉴学派的影响,1970年代以后的启蒙运动研究逐渐从纯“观念史”探究转向“观念的社会史”讨论。杨老师指出,最先创导这种转向的是美国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他在1971年即呼吁史学界从“观念的社会史”角度,更脚踏实地地审视启蒙运动,将其更精确地放在社会脉络和18世纪社会的实际情境之中。“观念的社会史”一个重要议题,是启蒙思想或观念的“社会传播”(social diffusion),即试图了解启蒙的种种观念如何从启蒙精英的圈子向下传播到社会大众。这个过程涉及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如识字率、传播媒体(报刊、杂志、小册子、图书)和公共领域(咖啡馆、茶馆、酒馆、学会、共济会)等。学者通过观察这些启蒙思想藉以散播入社会的工具,来对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和信仰的变化进行研究。
关于启蒙运动的断限,杨老师介绍了学界从“短时段启蒙运动”(Short Enlightenment)到“长时段启蒙运动”(Long Enlightenment)的转变。传统的“短时段启蒙运动”研究将启蒙运动限于18世纪之内,如德裔美国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所著《启蒙时代》(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即聚焦于1720年代至1780年代。“长时段启蒙运动”的研究则延展了启蒙运动的断限,如美国学者伦纳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就在《国王和哲学家》(Kings and Philosophers)中将运动的起始时间向前推至1689年。德国学者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启蒙运动的宗教起源》(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Enlightenment)一文中将启蒙运动的起源追溯到欧洲宗教战争结束的1650年代,并一直向后延伸至1830年代。波科克(J. G. A. Pocock)则将启蒙运动向前追溯至英格兰清教徒革命结束后的1660年代,认为此时英格兰教会为避免宗教极端而主动改良,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条件。
随后,杨肃献老师谈及西方学界对启蒙运动“一元”与“多元”的讨论。首先是关于启蒙运动在各国的发生情况。在20世纪中叶,学界主流一度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元的、以法国尤其是巴黎为中心的文化现象。持此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英国史家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而彼得·盖伊则形象地将欧洲各地的启蒙运动比作“family”,认为它们都来自法国,有共同的基因。1980年代开始涌现出一批强调启蒙运动“多元性”的研究著作,如英国学者罗伊·波特(Roy Porter)所编《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不过,杨老师也指出,“多元性”的研究趋势也导致了启蒙运动研究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启蒙运动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这个问题,也成为学界考虑的对象,继而引出若干研究成果。
“一元”与“多元”之争,也表现在启蒙运动参与者和影响者的阶级问题上(High or Low)。代表性成果有达恩顿的论文《前大革命时代法国的上层启蒙与底层文学》(High Enlightenment and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和其著作《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等。
“一元”与“多元”之争的第三个层次,是对启蒙运动内部性质(温和或激进)进行判断。代表性成果有英国学者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巨著《激进启蒙:哲学与现代性的形成》(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和美国学者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所著《激进启蒙:泛神论者、共济会与共和派》(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Pantheists, Freemasons and Republicans)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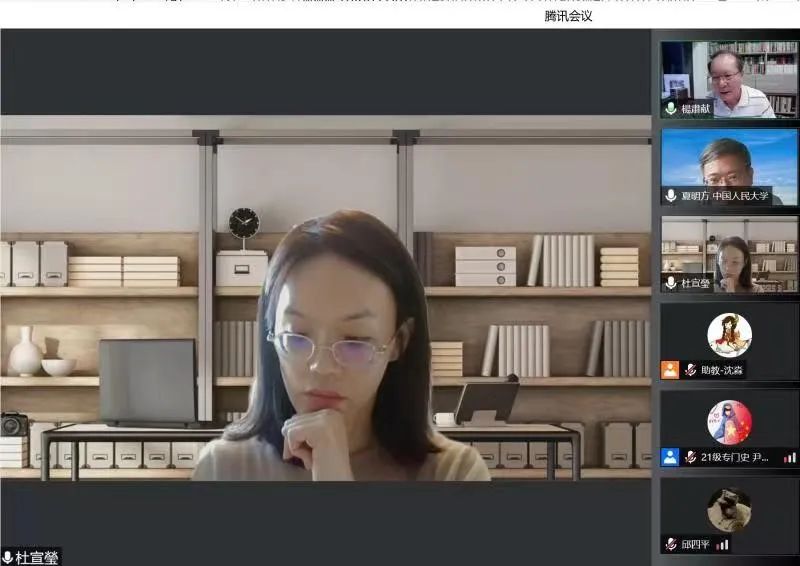
与谈人杜宣莹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指出启蒙史研究的转向处于西方社会经济史蓬勃发展、普遍强调历史语境的大背景之中。18世纪档案逐渐超越传统的教会或政府档案,更多地囊括底层、多元化的档案,这也是18世纪以降社会史研究成为可能的原因。杜老师还提到了福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并从知识的普世化和启蒙运动的大众反应两个方面对当前启蒙运动研究提出质疑。
最后,杨肃献和夏明方两位老师又提及启蒙运动的全球性角度。夏老师认为,启蒙运动看似是个老话题,实则常谈常新。其影响范围不仅限于法、英、荷、德等欧洲国家,还扩散至亚洲等地。启蒙运动是影响到全球人类命运的重大思想文化事件。杨老师指出,学界最新的“全球启蒙运动”(Global Enlightenment)研究,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等亚洲地区的启蒙,看作“全球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很显然,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研究尚无已时。
(撰稿:胡金凤、张君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