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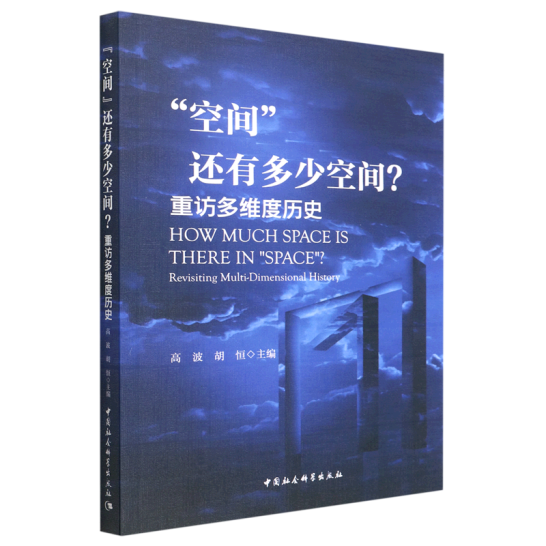
书名:《“空间”还有多少空间?重访多维度历史》
编者:高波、胡恒
丛书系列:人大青年史学工作坊“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内容简介
“空间”是现代人文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各专业领域历来不乏深入的研究。本书以“‘空间’还有多少空间”为标题,邀请当下活跃于环境史、城市史、人类学、艺术史、考古学、政治史、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十余位青年学者撰文,呈现当下“空间”研究的多样性,探讨各领域间呼应、互动与合作的可能性。依照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向,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聚落、自然与文化的互塑”、“图像中的空间呈现”、“画土分疆与王朝治理”、“信息流动、话语表达与权力空间”以及“葬域的多重结构”。编者、作者希望与读者探讨的,既是“空间”研究的空间,也是人文学本身在现代世界中的空间。基于这一主题的开放性,以上五部分的划分乃至每一部分内部的顺序,在阅读时都是可变的,请读者依照兴趣自由探索。
编者简介
高波,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曾于2018年春季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2019年春季赴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学。近年出版专著《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发表论文《晚清理学视野下的英国殖民秩序》、《晚清京师政治中“同治”话语的形成与变异》、《“中体西用”还是“中西同体”:儒学现代转型中的普遍历史叙述》等。近期研究兴趣为元明以降的自然、文明与政治思想,侧重时空观念与历史叙述、经史之学与思想史的互动。
胡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兼任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所副所长。2020-2021年为斯坦福大学Walter H.Schorenstein亚太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出版专著《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合著《百年清史研究史·历史地理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主要从事清史、历史地理学、数字人文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近期主要关注清朝国家治理的空间逻辑、基层组织演变史等问题,参与建设大型史学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统。
目录
导言 探索人文学的“空间”
聚落、自然与文化的互塑
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魏兵兵)
资源、环境与权益——天津墙子河的近代排污转型与影响(曹牧)
作为他者的环境——早期殖民者对澳大利亚环境的认知与利用(费晟)
图像中的空间呈现
位置、组合与意义——汉代西王母神性的图像观察(王煜)
马王堆帛画中双龙构成的“壶形空间”考(朱磊)
没有城市的城市空间——沈周《东庄图》及其图像传统(吴雪杉)
画土分疆与王朝治理
西汉桂阳郡阳山侯国、阴山侯国考辨(马孟龙)
初唐都督府的置废(罗凯)
“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明清州制新解(李大海)
信息流动、话语表达与权力空间
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仇鹿鸣)
哀荣——8世纪中叶一位节度使的丧葬罗生门(李碧妍)
从王权政治到君主共和——苏格兰玛丽女王之死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政权转型(杜宣莹)
葬域的多重结构
中山王的理想——兆域图铜版研究(莫阳)
从双室到单室——魏晋墓葬形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耿朔)
从“门窗”到“桌椅”——兼议宋金墓葬中“空的空间”(丁雨)
导言:探索人文学的“空间”
一
本书是一本非典型的论文集,它诞生于一次非典型的学术会议。2015年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史学工作坊以“‘空间’还有多少空间?——重访多维度历史”为题,邀请了环境史、城市史、人类学、艺术史、考古学、政治史、历史地理学等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共同探讨,通过“空间”这一人文学各领域共有的母题,探讨人文学乃至学术生活的新可能性。
这种设想,部分出于发起者对下学术生活的共同经验与意识。现代人文学的世界,其广阔已非任何研究者所可遍历,其分化程度与绩效压力,更让研究者难有机会走出其专业领域。
这一境况,从一方面来说是学术发展的题中之义,毕竟正如斯宾塞所说,进化的一大特征即是不断的分化。但另一方面,人文学乃至学术生活,又有着内在的对整体性的吁求。而相较于更为专业化、学科限定也更为明确的研究所,大学的奇妙之处则在于,除了拥有多元而优秀的学生,它还促成了不同领域学者的汇聚。在学术世界中位置遥远,在现实世界中,则可能鸡犬之声相闻。而与《老子》所描绘的上古时代不同,相闻就总有往来的可能性,日常从研究领域差异巨大的同事与朋友处受到的启发,有时是如此意外而令人惊叹,令人恍惚间感受到作为学生初入行时经常体验到的那种面对广阔而浩渺的人文学世界的惊奇乃至震惊。
这里所谈的,并不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跨学科”问题。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前提下尝试跨越它,往往发生在邻近学科,“跨”的行为往往有着明确的知识意图与学术指向,事实上,也只有学术距离仍相对接近,“跨学科”才是现实的,才有在一定时期内获得成果的可能性。不过,正如一位朋友的妙语,对不同学科采取“横跨”的姿势,既不优雅,更不舒适。而在不断分叉的学术进化树上,越远离地面、接近树冠,不同枝杈间的距离就越远,“横跨”也就越危险甚至不可能。换言之,“跨学科”只能发生于可望又可及的学术领域间,而在学术分化不断加剧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学术领域正变得可望而不可及,甚至不可望亦不可及。结果则是一方面对某一个细分领域过度熟悉与沉浸,另一方面,则是对其他领域的完全陌生。当下不少学者主张以去熟悉化与重新遭遇惊奇作为新学术思想的起点,大概正是痛切于此。而重新遭遇那些陌生的研究领域,自然是对本领域去熟悉化的最可能途径。简言之,相较于邻近学科间的“横跨”,重建学术世界内中远距离研究领域间的联系,就显得更为迫切。
一个可能的启示来自古代。在宋儒处,有两种似相反而实相承的人文世界之理。一方面,在朱熹看来,“理一分殊”,“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 学者对其各自研究领域的沉潜与坚守,可谓穷其各殊之分,实为呈现理一之境的前提条件。而另一方面,在张载看来,“太虚即气”,“所谓气也者,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 “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 距离遥远的研究领域,通过这无限、无始又无终的太虚之气的氤氲聚散,不断互相感应熏习,亦就在不知不觉之中互相影响与改变。而相较于宋儒的“极高明”,汉儒所论,则更为平实。郑玄以“仁”为“相人偶”,更具体言之,即“以人意相存问”, 而仪礼聘问中主宾相揖,则为其典型。主宾各有其邦国,往往相距千里,而亦惟其邦国不同,相距遥远,故当以揖让而相偶,以达成仁礼之一体。
这大概也说明了为何近年来王汎森等学者特别强调历史与学术中无形无相的“风”的重要性。王汎森以历史的联系往往隐秘而微妙,多有“铜山崩而洛钟应”之事,故需要“察势观风”,方能远近大小,各如其情; 而在将“风”当作历史观察与研究的珍贵视角之外,他更视其为人文学自身的养成之法,强调“龚自珍《释风》篇中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这种日常接触与交往中动静相感而又无形无相的“风”,让日常世界与学术世界良性互动,亦让学术的可能性与意义得以自然生长。
大致说来,以“空间”为主题词,就是想为来自不同学术邦国的学者们提供相偶而存问的机会,以促成学术世界中无形之风的氤氲蒸郁。而空间这一“主题词”的选择,与这一目标之间,又有着不止一层关系。一方面,以上对现代人文学演化图景的描述,引申出学术与距离等空间因素的辩证关系,故而用“空间”作为主题词,虽非有意设计,却恰恰呼应了这种对学术养成的体验。而另一方面,“空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近代词汇,有着一望可知的近代物理学背景,正如柯瓦雷所说,整个近代世界都建立在一场根本的空间革命上,古典意义上万物各有其位的封闭而稳定世界,被在尺度上无限延展的宇宙所取代,在这一笛卡尔-伽利略-牛顿所揭示的数学化、均质化与去中心化的新世界中, 空间意味着无物的虚空,它是纯粹被动的,也自然没有任何象征着人文世界的气与风能够存在。
这可谓是人的去世界化,实为人文学世界中各邦国成员都需要面对的共同挑战。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叶,麦克斯韦在电磁学引入了“场”的概念,空间不再是纯粹被动的,而是可以施加影响于事物,到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则正式取消了空间与事物两者间的独立性,事物亦可影响空间的构造,但以上自然科学的伟大进展,并不意味着人的世界的回归,相反,正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不同地方又称为精神科学、价值科学)的分离日益明显,而约一个世纪后C.P.斯诺以科学与人文为互相分离且鸿沟甚深的“两种文化”,则不过是对这一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的迟到确认。
故而在人文学中思考“空间”范畴,天然就带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而此种关系,在环境史、考古学、城市史与历史地理学等“横跨”自然与人文的研究领域中,自然表现得最为充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立乃至对立,既让“横跨”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也同时意味着超越这一分立乃至对立的新探索,最有可能出现在这些研究领域。正如拉铁摩尔所论,不同地理与文明间的边疆地带,即是两者发生交换与混合的贮存地,打破既有格局并开创新局面的势力,往往即从此处崛起。
另外,如果说环境史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自然界前所未有的大扩张关系密切,人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全球性殖民扩张的产物。而与前述天上空间从封闭世界向无限宇宙的转变不同,伴随着西方的崛起而发生的大地空间的扩张,则因为地球的有限性而有着明确的边界。这带来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新理解。一方面,大地看似广阔但终究有限,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自然以指数增长的需索,严重冲击着长期演化而成的万物秩序,以自然的有限性与有序性为名展开的对这一无限制需索的反思乃至反抗,可算是环境史得以出现的思想前提。另一方面,西方的全球性扩张,将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明卷入新的世界秩序,这种半强迫性的不同族群与文明的“遭遇”与冲撞,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反复上演且强度日增,在此背景下,以理解“他者”为职志的人类学,也才有了出现的必要。
这尚不是近代空间革命与人文学关系的全部。如果说均质化与去中心化的“无限虚空”让宇宙对人完全外在化,从而直接威胁到人文世界的存在与意义,与此似相反而实相承的则是空间被视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范畴。康德主张空间与时间是人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与“先天知识的原则”,以此为启蒙理性与现代学术立法,而在一个多世纪后,科塞雷克则进一步说,人无法直接经验时间的存在,只能借用表达空间变化的范畴来间接呈现时间。 如此则空间就可被视为比时间更为直接也更为基本的经验与思想范畴。而艺术史中反复出现的以空间呈现时间的尝试,以及政治史中对权力正当性与作为感性知识来源的“看”的关系的探讨,则都体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现代人文学的主要奠基者维柯看来,真理即创造,故而相较被视作上帝创造的自然,人只能对自己所创造的人类世界有完全的理解。 而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的真理性就和它的作品性紧密相关,且此一作品性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而关涉所有人类活动。空间的构造自然亦不例外。如此则空间实为人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二者为融合而非对立的关系。考古学领域以墓葬为作品的尝试,即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既外在又内在,既疏离又切近,这或许就是空间与人乃至人文学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对人有两个著名的规定,在《形而上学》开篇,他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而在《政治学》第一卷,他又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如果说在现代世界中,求知变为不断冲破自然加于人的限制,达至无限大、无限小、无限高亦无限远之处,那么人作为政治的动物,则意味着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他/她只有生活在一个有着确定边界的空间内,才能够创造真正属于人的世界。而如果说历史地理学中的政区研究、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乃至人类学中的村落与城市研究,尚只是在引申意义上表明了这一人类生活的有界性与境遇性特征,那么,政治史对政治行动与各种空间因素的关系的探讨,则更为直接地呼应了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
最后,让我们回到现代中国学术的开创时代。上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一面主张要“如欲彻底的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 另一面则提倡以合传的形式改造旧史,并以人物为中心写作新通史,甚至说要“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 傅斯年则更直言“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 都将空间与人当作是新学术互相支撑的两翼。在此意义上,本书以“空间”为主题,而其中篇章多以人与空间的互动展开,可谓是对这一已历时百年的新学术传统的自觉回归。
二
本书所收入的论文,来自学术世界中的多个风土与人情均判然有别的邦国。两位编者亦只是充满兴趣的旅行者,并不自诩能对它们做出恰切而专业的把握。不过,提供一个概略性的导览或许仍然是有必要的。毕竟,对旅行者来说,最能激发兴味、引起共情的,往往是其他旅行者的观察与思考。
本书的第一个主题,为“聚落、自然与文化的互塑”,在具有政治、族群与文化多重特性的城市与乡野空间中,考察人与自然的互相塑造。当两种或多种文明遭遇时,不同因素混杂并置,互相竞争、对抗、合作与重组,会生成特殊的空间结构。而其典型形态,则是文明交界处的城市。郑少雄从“景观的建构”和“景观的生产”两个面相入手,考察中华帝国晚期康定从贸易港、土司城到近代城市的功能转变,探讨前近代时期亚洲内陆的族群遭遇与互塑,以及地方社会对汉藏族群相处模式的认知。郑少雄发现,如康定这样的汉藏文化交界区,城市空间具有多层次的混杂性(不仅城市整体是混杂的,城市的每一个局部也是混杂的)。他所着力呈现的,是这种文化混杂如何得以景观化。有着复杂背景的传说与故事塑造着康定城这一文化互嵌的空间,在不断再边界化与去边界化的过程中,混杂共存逐渐演变为多元一体,景观得以呈现自身,而“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也得以形成。换言之,不同文化的嵌入式涵化,有赖于在文明交界处的城市空间中展开的排斥与融合的辩证法。
在近代西方全球性殖民扩张的背景下,这一文明遭遇更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此即阿里夫.德里克所称的“接触地带”。而不管是魏兵兵所探讨的上海租界剧院,还是曹牧所探讨的天津租界的排污河,都是其典型案例。魏兵兵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华界精英对华人剧场的建筑变革为研究对象,探讨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的演进过程,展示其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在他笔下,公共剧院作为现代性的空间安排,性别、阶级与族群意义上的敞开与封闭、禁锢与开放并存,在这里,不同的观看/被观看方式,创造着权力展示、循环与再生的空间,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社会构成方式。作为特定公共空间的剧场由此呈现自身,而它所激起的中国传统的回应,也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曹牧通过对天津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墙子河的考察,探讨借助自然因素构建出的区隔性空间秩序。她提示我们,在天津这一“接触地带”,租界内嵌在既有的城市秩序中,却隔绝并排斥城市的其他部分,殖民者通过切割出所谓“干净的”排污渠,保证污物的单向流动,从而将本可成为连通渠道的河流,变为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的分隔线。换言之,城市水系这一人化自然,被以清洁/污秽的名义重整,成为社会排斥的工具,伴随着水闸、河堤等城市景观出现的,是权力对自然的操纵,其结果则是一种附着在城市空间上的殖民等级制。
与异文明间的遭遇不同,费晟所关注的,是人与荒野或者说文明与自然的遭遇。他通过对早期澳大利亚殖民者(囚犯、自由定居者、官员与专业人士)对环境的多样性认知与实践的考察,提示我们对自然来说,殖民者的到来可谓是一场人对荒野的入侵,而反过来,文明社会又会生成否定自身的意识,将走入荒野、投身自然当作是自由的象征。定居地通过交通网络互相连接并分隔荒野,而荒野又以更大的尺度与耐心包围定居地,自然空间与人类空间互嵌互渗,既对峙又交融,殖民者既改造荒野,也被荒野所改变,最后,则出现了何谓家园的问题,而异乡的家园化,反过来就是家园的异乡化,人类与自然相克相生的辩证结构则由此呈现自身。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为“图像中的空间呈现”。这种图像空间所呈现的,则往往是时空综合体。王煜通过对汉代西王母图像的考察,尝试展现汉人对生前世界与死后世界的总体看法。西王母图像中的主题内容、相对位置、大小比例、运动趋势等,均有着从生活世界到神圣世界的秩序与仪式意涵,识别其空间结构与先后次序,如同随古人在其信仰世界中瞻拜行仪。
与王煜类似,朱磊通过对帛画中壶形空间的考察,提示我们图像必须被当作有着内在逻辑与生命的整体。图像的空间结构,经常呈现着古人信仰世界中的修炼步骤或仪式过程。因此,起始视点(同时也是入手点)以及视线方向(同时也是行进方向)就十分重要。而为了复现这一以空间形式展现的时间过程,读图就不能抽取局部元素孤立分析,而必须是整体与部分间不断的解释循环。
吴雪杉所关注的,则是观看者的角色与“看”的多样性。他以明代画家沈周的名作《东庄图》为对象,通过探讨其对城市空间、山川景物以及观看视角的处理方式,透视明代以来“城市山林”的图像传统如何得以塑造成形。他所着力呈现的,是理想性的山林景观如何与现实中的城市融合。正如贡布里希笔下的埃及画家认为每一事物都有能最充分与真实地展现自身特性的典型视角,故他们在作画时并不遵守单一视点原则,而是将人脸各器官从各自的典型视角纳入同一幅图像, 吴雪杉笔下的明代士大夫,也是通过理想性甚或姿态性的空间叠合,将其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部分,以符合其世界观的方式呈现于同一幅画作中。而也正是这种观念性的“心眼”对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交融性展现,让明代士大夫得以极高明而中庸的儒家式姿态调和精神与世俗,以超越与出离的姿态安享于日常生活。而通过揭示这种打破几何视点的空间重组方式,吴雪杉则呈现出了“看”本身的多样性。
如果说上一主题展现的是空间与观看的多元关系,本书的第三个主题关注的则是如何划分和命名空间,或者说,是空间与名称的关系问题。其题名“画土分疆与王朝治理”,更表明这一划分与命名活动与政治过程密切相关,其中时间与空间、名与实的互动至为复杂。大体而言,封建制下秩序空间的演变更多因循故物与故名,而郡县制则有更多的循名责实色彩。马孟龙通过对西汉桂阳郡阳山县县名的探讨,透视在封建与郡县混杂而郡县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西汉时期,政区空间不同要素各自名与实的演变轨迹。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时期的政区变动往往不是局部与自发的,而是与更为整体性的地理与制度格局密切相关。因此探讨政区名称的演变,就必须考虑郡县与封建两制不同的空间构成逻辑与演变理路,以相对不变的山川为参照,同时结合地理与政区命名与注释的知识传统,才有可能真正复原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区空间秩序。
与马孟龙类似,罗凯的研究同样关注政区空间秩序的演变问题。他通过对唐代边疆地区都督府置废问题的探讨,揭示了大一统帝国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秩序具有不同的政治特征与演变轨迹,固定或多变,常设或暂时,其历史意涵判然有别。如果说因为统治能力的限制,边疆地区空间秩序的临时性多是不得不然,那么中心地区空间秩序的临时性则往往是有意为之。小大相维、内外相制的原则,体现在政区空间大小、历时久暂的不同安排之中,既可以被理解为具有特定王朝印记的统治术,又受到跨王朝制度演变理路的影响。
李大海同样关注政区演变中空间与时间因素的互动,不过,他所关注的,已是郡县制全面成熟的明清时期。他以此一时期的州制为对象,从出自《周礼》的“体国经野”和“设官分职”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角度,探讨《清史稿·职官志》所谓“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一语的含义。他认为,州这一介于常设的府与县间的政区,集中体现了郡县制下名实、常变、经权诸组关系的复杂衡平。在特定政治秩序下,权力运作的内涵与空间差异密切相关,探究影响政区空间的层次、比例、久暂的因素,可以透视郡县官僚制下行政效率与权力制衡的两难。而空间秩序演变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又与王朝内与跨王朝这两种时间尺度相联系,相当鲜明地体现出郡县制下政区作为时空综合体的一面。
如果说政区的空间性显而易见,政治本身的空间性则相对要隐晦一些。而本书的第四个主题“信息流动、话语表达与权力空间”正是要探究政治与空间的隐秘联系。李猛认为在传统政治中不是合法性而是“政治表象”(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居于中心地位,如同吉尔茨式的“剧场国家”(the theatre state),表演性的政治仪式“使君主得以成为全民眼睛的焦点,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世界的示范中心(exemplar centre)。” 仇鹿鸣对唐中后期魏博的政治景观的研究,正是聚焦于权力本身的空间可见性以及观看者的重要性。与政区借以呈现自身的几何化与抽象化地图不同,魏博的藩镇节度使祠堂、刻石乃至德政碑是更为具象化的景观。而与费晟所关注的荒野中的文明景观不同,德政碑等不可能自下而上自发形成,而一定是权力的有意造作,它们预设了观众的存在,从而既是实存的,又是仪式性与表演性的,如同权力的公共剧场,通过这一假想或实际的剧场与观众,权力秩序在呈现自身的同时,亦完成了交换与再生产,政治斗争则必然伴随着以政治景观为中心的空间秩序的象征性重组。而若结合以巫鸿对石质建筑被视为具有永恒意味的纪念碑这一西方观念的批判性反思, 则时间尺度问题就呈现了出来,不管相较王朝兴衰还是更长程的文明与历史演变,这些仪式性的刻石与德政碑都是有朽而非不朽的。
如果说仇鹿鸣探讨的是政治空间的可塑性的话,李碧妍则通过对一位中唐官员的墓志的细致解读,展现了相对稳定与公开化的地理空间对隐秘而多变的政治过程的解码作用。在她看来,史料批判必须以敏锐的时空定位意识与能力为前提,墓志记载中时空异常的痕迹,如同当事人留给后世的密码,通过类似侦探复原案件现场与过程般的回溯性研究,我们有可能接近当时人不同撰述的背景与意图,而隐藏在厚重历史帷幕后的特定政治过程,也有了呈现自身的可能性。
政治的空间性与遭遇性,与人活动能力的有限性密切相关。这一问题尤见于在传统社会中受到更多限制的女性。彼时男女之别被自然化为外与内、可见与不可见之别,对女性的空间限制被认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政治则被认为属于公共与可见的世界,故而女性身份与政治职分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针对这一问题,杜宣莹聚焦于英国都铎王朝后期,探讨了此时政权从内廷转移至政府的过程中伊丽莎白一世与男性官僚为争夺政策主导权而引发的公开冲突,集中分析伊丽莎白一世与枢密院的信息获取斗争,强调在以内廷与外朝之分为基础的政治空间中,连接两者的通道与开关具有极大的政治重要性。名义上的王权必须克服由于女性身份而带来空间限制,防止信息阀门被其外朝对手所控制,而这种围绕政治空间的通道、阀门与边界的斗争,又必须借助王权神圣性与性别特质的政治话语而展开。
如果说自然划定了人文学的一条基本边界,死后世界则划定了另外一条。故而与本书的开头呼应,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就是“葬域的多重结构”。对古人来说,死后世界既是生活世界的他者,又内在于后者本身,且恰恰因为它划定了生活世界的边界,才使自己成为后者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这也正是莫阳的研究所提醒我们的。莫阳通过对中山王兆域图铜版的考察,展示了墓葬作为墓主作品的一面,营造墓葬空间,就是呈现特定政治与人生秩序,并表达墓主个人的希望与追求。在莫阳看来,兆域的建筑尺度与几何对称性布局,是通过形式美学展现统治秩序,而兆域图亦非葬域空间秩序的简单比例缩略,而是以凸显具有天道意涵的俯瞰视角为目标的再加工,故而也应被视为具有个人意志与风格的独特作品。
与莫阳类似,耿朔也探讨了墓葬作为礼仪空间的观念性与作品性。他通过对魏晋墓葬从双室到单室的转型过程的考察,提醒我们注意墓葬的广狭、形制以及其与地面建筑的关系,与所处时代的生死观念密切相关。在历史早期,人的死亡被视为形与神的分离,故而相较于掩埋形体的墓地,形与神重新相逢的庙被视为更重要的祭祀空间。而在汉魏时期,伴随着生死观念的改变,神被认为亦在墓内,生与死、地上世界与地下世界被认为互相沟通而非隔绝,与此相伴的则是礼仪空间从庙转向墓,墓上乃至墓内祭祀的出现、墓葬整体与单个墓室空间的扩大皆与此相关。另外,耿朔亦提醒我们生死观念与葬域秩序的多元性,他注意到墓室中假窗在不同时期与地域交替出现与消失,故认为将墓葬视为死者的地下常居还是只是其暂时的寄居之所,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这种多元性,亦体现了葬域之为特定文化与社会的群体性作品的一面。
最后,丁雨通过对宋金时期仿木构墓葬的解读,亦试图发掘葬域空间的多重含义。他借鉴弗雷泽对以模拟与接触为特征的顺式巫术的经典探讨,分析墓葬后壁装饰中启门、桌椅等元素的功能性与象征性意涵。启门作为生死世界的边界,既象征隔断,又隐喻开启。桌椅则作为墓主对(并)坐之象,提示着祭祀灵位的所在。这是死后世界对生前世界礼仪性活动的象征性模仿,它所模仿的,并非该仪式的全部过程,而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某一时刻,且这一死后仪式本身只有布景与道具,而没有行礼者,故丁雨称其为“空的空间”。也正是通过这种“空”的存在,礼仪的象征与实际、死后世界与生前世界的区隔与联系被辩证性地呈现了出来。
以上就是两位编者所做的挂一漏万的导览。可以看出,作为遭遇、作品、景观与时空综合体,更统而言之,作为人所创造又在其中定位自身的世界,空间多元而丰富的内涵,提示了我们书写多维度历史的可能性。而作为人文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空间的多样性与生命力,则让本书“‘空间’还有多少空间”的设问,在文字之戏外,更具有了严肃的意义。询问“空间”的空间,也就是询问人文学本身的空间,而诸位作者则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做出了各具性格而又互相呼应的回应。
******
如前所述,本论文集为2015年秋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同名学术会议的后续。收入本书的论文,都曾在该次会议上宣读过,非常感谢各位作者的支持。青年史学工作坊的诸位同仁,虽兴趣与性格各异,却因对当下学术境况的共同经验与意识,一起推动了会议的召开与论文的结集出版,这是友谊与共同经历的见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会议还是论文集,陈昊的策划与推动都是最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他的学术视野、活力与耐心,这件事就不会开始并实现。
(导言注释从略,如需引用,敬请参考原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