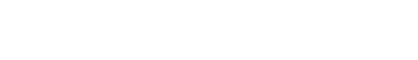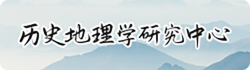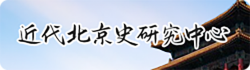新闻动态
会议纪要 | 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底层女性叙事
发布:2025-07-11 来源: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2025年7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院、清史研究所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新书《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研读会。本书作者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马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毛立平、杨剑利、刘贤、胡祥雨、高波、张燚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湛晓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韩晓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等参加讨论。研读会由清史研究所王建伟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院校近三十名师生参加。

马钊首先介绍《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一书的创作背景与研究初衷。该书作为其博士论文成果,英文版于201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2025年推出。本书主要基于北京市档案馆“妨害婚姻与家庭罪”档案。研究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是希望把北京作为“城市”而非“帝都”来研究,呈现其中的个人与城市的关系,关注底层群体,以小人物故事还原城市生活。第二是受苏成捷、白德瑞等法律史学者启发,通过司法档案挖掘底层女性的生存故事。在阅读档案的过程中,马钊发现法庭对话中存在两种文化体系的对撞,法官使用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话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话语体系,而底层当事人则沿用传统表述。因此,需要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把这段历史作为一个文本去阅读,了解文本的生成路径。

毛立平认为书中对档案的运用十分有趣,通过城市底层女性犯罪档案,展现小人物丰富多彩的生活,打破了以往对历史上女性思维意识固化、落后的认知。她称赞了马钊“讲故事”的处理方式,将不同类型女性的生活交织呈现,由此展现出时代的新与旧、内与外、传统与现代的冲击。尽管书中所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但作者很好地呈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底层女性身上既有旧的传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毛立平认为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女性情况各异,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女性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自己的生活,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拓展生活和生存空间,体现出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能动性。清代女性可以利用法律空挡为自己争取有利判决,民国时期底层女性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权利有限,但依然活跃并能动地应对社会变化。针对马钊作为男性学者研究女性史这一情况,毛立平提到,男性学者参与女性史研究可能会被认为不懂女性,但男性可以提供外部视角,与女性内部视角互补,内外兼修方能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韩晓莉认为,本书是将“弃夫潜逃”现象作为线索,对当时北平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考察上层治理逻辑与下层生活策略之间的互动,叙事生动且颇具可读性。书中涉及的职业问题、城市贫困化、犯罪、交通、身份证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同时,韩晓莉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提示马钊可以关注民间口述故事中有关底层女性的叙述,并进一步提到“潜逃”这一行动得以成行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底层女性可以通过邻里网络、人贩子关系等实现潜逃。底层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对立,也有共谋,女性潜逃的通道往往会有很多男性的参与,其中生存与道德的平衡点是很微妙的。韩晓莉认为,193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强调抗战时期北平作为“孤城”的特殊性。尽管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但北平底层社会对政权变更的感知力并不是很强,底层人民反而可能利用动乱来谋生。韩晓莉提出了可以继续思考的几个问题:其一,1930年代北平贫困化问题突出,贩卖女性的犯罪问题在战前与战时是否有明显的变化?其二,在处理相似案件时,不同政权的态度是否不同?其三,犯罪成本是否会成为女性行动的考虑因素?其四,不同政权下执法者的差异对妇女生活和犯罪的影响,以及执法者与案件当事人的互动问题。
胡祥雨认为,本书以底层百姓生活为研究对象,通过众多细节成体系地展现了北平作为大都市的社会状况,涉及了工业、职业、交通、婚姻等多方面内容。该书在学术路径上与法律社会史研究相关,虽使用法律史材料,但更偏向社会史研究。他将该书与陈美凤的《法庭上的妇女》对比阅读,认为两本书结合能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妇女的状况。由此,他探讨了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法律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例如一夫多妻与形式上一夫一妻制的矛盾;同时,他还提出了几个问题:法庭中的妇女对法律的利用情况?书中未提及一妻多夫现象是因为案例被筛选掉了,还是城市与农村存在差异?虽然政权更迭,但法律制度上是具有延续性的,日本殖民统治对当时北平的法律实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针对前三位评论者的发言,马钊予以回应。关于司法档案的局限性问题,马钊指出,民国时期司法审判仅针对法律条款讯问,“弃夫潜逃”并不是一项罪名。司法档案记录有限,并不能呈现全面的故事,需要读者自行评判结论的适用范围。关于妇女的言说困境与情感表达问题,他认为民国时期底层妇女缺乏表达情感的词汇和话语体系,因此缺乏发声的机会与能力,处于“失语状态”。他还提到便利的婚姻并不意味着妇女有无限的可能,她们仍受制于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研究的结果不在于评价某种婚姻形态对妇女的利弊,而应聚焦她们做出抉择背后的社会、道德因素,这种抉择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冲突,以及这种体制对她们的判定。此外,他认为城市管理像一个大杂烩,由不同时期制度累积而成,制度设计的连贯性与积累性也是这本书要强调的部分。毛立平老师补充道,明清时期,底层女性对婚姻的核心诉求是“衣食无忧”,情感需求是奢侈的。若家庭无经济困境,夫妻关系即被视为“良好”,当时的妇女不在情感这套话语体系中。
杨剑利注意到交通网络的重要性,指出北平的铁路网络(如北宁线、京绥线)建设为底层女性潜逃提供了条件,城市道路的改善间接影响了人员流动的便利性。同时,她指出本书从结构上能看出国家意识的影响。关于性别问题,杨剑利表示每个人对性别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妇女自身对性别问题的认识也很不同。此外,她还好奇中国传统礼制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实践的,对基层社会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最后,她点明该书研究时段选择的深意,认为从市政管理的制度延续性角度考察,1937—1949年覆盖国民党、日伪、新中国政权,贯穿其中的是一条组织化、国家化的线索,若研究止于1945年,则无法完整呈现这一演变逻辑。
刘贤认为该书通过“个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将底层女性的劳动经济、大杂院人际关系、市政管理等纷繁复杂的内容串联,融入在一个大的框架之中。 同时,她肯定了书中纳入丈夫控告、人贩子参与等男性视角,避免单一女性叙事的片面性,这样多重视角的妇女史打破了政治史线性叙事。这是一部精彩的抗战生活史,也是一部迁徙史。她还提出疑问:北京与上海的世界主义有何不同?底层是否还有更丰富的人群?
湛晓白认为,本书可以反观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路径的转变。她肯定马钊老师运用社会史视角关注底层妇女命运,利用司法档案还原生活切片的研究取向。这本书给她带来扑面而来的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一方面来自于其对老舍等人作品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来自于她的个人经历。她关注到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城市具有的流动性、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女性潜逃提供客观条件,而农村熟人社会的特质可能使女性难以逃离。她认为,本书虽以抗战时期的北平为主,但其所展现的历史世界,在时间上,实际从清代一直绵延到新中国成立;在空间上,从街市、旅馆一直扩展至更广阔的华北地区。最后,湛晓白针对本书提出三点疑问:第一,北平妇女弃夫潜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现实层面的考虑还是掺杂了情感因素?第二,从法庭本身来说,妇女存在被歧视、语言能力不足、来自男性法官的性别歧视等弱势,她们在法庭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第三,这些女性的“原生家庭”对其遭遇的婚姻危机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赵妍杰为研读会提交了文字材料。她认为,马钊将案件置于抗战时期北平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司法档案重建底层女性的生活,展示她们在生存线上的挣扎,揭示了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这种方式打破了精英话语中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理想化叙述,让读者反思精英思想对底层的实际影响。这种关于女性家庭,以及战争对普通人影响的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深挖。赵妍杰提出了一个问题:家庭究竟是保护性的制度还是压榨性的存在?五四时期的激进青年认为小家庭是温暖的港湾,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小家庭却充满谎言、虐待、矛盾以及冲突。这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持续性的现象,是整个中国被裹挟到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副产品。同时,还她指出,司法档案如何定位、如何从“非常中寻找正常”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例如,北平普通民众中是否存在为孩子经营婚姻、将其苦苦带大的母亲呢?
张燚明以个人家族史为关照点,结合对该书的阅读体验,将书中关于民国北平底层社会的研究与其祖辈的生活经历相互印证,叙述了迁徙与交通、户籍与身份、居住与社区、劳作与生存、时代变革的影响等议题。同时,他提出本书对保甲制度的关注较少,建议可以进一步关注保甲制度下保长等基层人物的历史轨迹,以及北平小报中家长里短故事的史料价值。他感谢马钊唤醒了他对于儿时记忆的怀念,这正是历史学者的重要意义所在。
高波首先关注了本书的中文标题和英文标题之间的差异,指出“run away”是比“弃夫潜逃”更大的概念。其次,他指出近代社会是一个转型期,存在新道德与旧道德并存的“双轨制”现象,底层男性和女性都会根据利益选择道德话语,这种道德的灰色地带是沦陷区底层生存的底色。不同于James C. Scott所强调的农民反抗的道德正当性,本书中底层妇女的选择更多还是出于实用主义。同时,他认为,本书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法律、道德等内容更多体现在背景上,这与华南学派的研究取向有相似之处。随后,他指出这些女性作为“城市底层”具有乘火车、上法庭等能力,与县城、乡村女性已有不同,这体现了北平的城市性。他又以舞女在北平和上海两座城市的不同象征,说明了北平的保守性。此外,北平的保守性还体现在日伪的统治方式上,这与北平存在大量北洋前清遗老、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有关,这种统治方式导致了其司法实践与南方存在差异。最后,他对本书提出两点疑问:第一,书中强调女性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叙事的边界在哪里?结构性的叙述与个人主体性之间边界在哪里?第二,是否存在“合法逃离”的现象?司法档案是否遗漏了丈夫主动配合的“非刑事”逃离事件?
对谈结束以后,在场听众针对日伪政权的意识形态与五四以来强调妇女解放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妇女农业化对于“弃夫潜逃”的影响、档案及史料的收集和选择问题、丈夫控告逃妻的经济动机、爱情电影对于中国爱情文化的影响等问题与各位老师展开热烈的交流。
马钊对此进行集中回应。关于日伪政权的意识形态及统治影响,他指出,日伪统治在书中主要作为背景,主要以执法者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形式体现。日伪政权并不强调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话语,北京地方法院依靠的主要还是民国以来的法律体系,这里面带有较多的五四色彩。关于城乡差异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生活空间主要还是在城市,而城市底层社会同样建构着这个城市,运用法律档案研究底层社会有助于理解我们生活的空间。针对本书的档案及史料选取问题,他回应,他的研究受苏成捷的启发,加上对北京熟悉的原因,选择了北京关于婚姻家庭的司法档案,优先选取包含更多社会史信息的长卷宗。他认为对十三年里四百多个出走被抓的案例进行量化处理意义不大,侧重从案件中提取更多的信息。关于丈夫将妻子告上法庭的动机问题,他指出底层人结婚本身就有买卖婚姻的因素,控告的动机很大程度出自经济因素。关于电影如何影响底层情感文化的问题,他指出底层是一个空间,而非一条线,以当时的物价指数,底层人民也能看得起电影,但所见档案并未涉及观影类型。
王建伟借助近期上映的电影《酱园弄》,指出电影和今天讨论的《弃夫潜逃》形成了很好的呼应。这体现出女性在面对情感困境时具有多种选择:弃夫潜逃、离婚、甚至杀夫。毛立平补充道,女性并不是没有情感,只是在弃夫潜逃的案件中,因情感需求而潜逃的例子较少,并且通过司法档案可以观知,当时的司法体系也没有留给女性表达情感的空间。
讨论环节结束后,王建伟对本次研读会进行总结。他指出,今天的研读会解决了很多问题,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这种循环往复是学术发展不竭的永恒动力。近代北京城市史具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不同立场、不同视野的研究议题都可以纳入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院将继续在这一领域深入拓展,持续推出更多的高水平学术成果,为北京的城市史研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