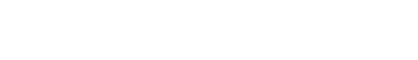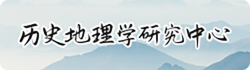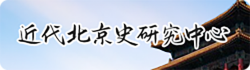彭凯翔: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
发布:2011-09-08 来源: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
———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
彭凯翔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475004)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火神会账本中的货币与价格史料出发,结合其他直接、间接史料,对近代北京的货币行用状况与价格结构变化进行探讨。在货币行用方面,本文试图说明“京钱”的记账本位币性质,明确它的减值与贬值过程。与京钱相对应的有各种名目的实货币,虚实货币共同构成了近代北京的货币体系。随着该体系的蜕变、瓦解,北京经历了持续的通货膨胀。通过火神会账本中的以及其他现有的物价工价数据,可以对通货膨胀中的相对价格变化有更准确的认识。此外,本文结合当时币制和经济体系的特征,对通货膨胀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账本 京钱 虚货币 实货币 通货膨胀
国家图书馆藏有火神会及火祖会账本数部,凡十七册,覆盖的时期为道光十五年(1835 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 年)。① 账本不仅反映了北京火神会的组织运作状况,还提供了当时货币行用及物价等方面的信息。以往在讨论近代北京的货币及物价时,多从官方档案、文人笔记以及口述史料等入手,相反,第一手的账本除甘博等人的早期研究外,甚少系统梳理。本文希图从火神会账本出发,与其它史料、研究相激发,来增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账本简介
现藏账本分属于两个火神祭祀组织②,分别为火神会和火祖会。火神会的成员主要是城区匠作行的各厂、各号、煤铁铺以及灰局,常有三四十号,少时二十来号,至民国初已呈式微。火祖会的成员较复杂,包括各府宅家户和各商号楼堂两部分,常有百来号,民国十五年更达到一百五十四号。火神会有大会首与副会首,会首轮值,但会员既不固定,会首也无法完全按序轮排,如万成号在咸丰六年至同治元年这七年间就曾三任会首。火祖会员则有大户、散户之别,大户助钱多,散户按较低标准统一纳钱,会员亦不完全固定。显然,两会均非托名神圣的同业或同乡组织。其主要功能只是操办祭祀,可因祭祀而聚会,自然也会有联谊的作用。
民俗多以六月二十二、三日为火神祭日,账本亦以
显然,火神会账本对于民俗史、商业史等多种研究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不过,本文的主要兴趣在于,账本的延续性提供了成序列的货币、价格史料,从中可以窥见近代北京货币行用的变迁和物价结构的动向。就此匿名的序列史而言,无论是火神会账本,还是其他厂号账本都是相通的。所以,本文将结合这些账本中的同类信息,来获得更一般的认识。同时,货币和物价的变化不仅是火神会账本中的主要内容,而处身币制变革时期,选用合适的记账货币、根据预期价格来调整香资和开支等等,对于火神会的日常运作也至为关键。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可作为对该具名账本的另一种解读。
二、记账货币
晚清民国,北京地区行用的货币大体可以分为银、钱两类。一直到民国九年以前,火神会账本均以“文”为记账单位,相应的记账货币无疑是钱。然而,作为记账本位的货币或虚货币④,它与实际流通的货币即通货并不是一回事。例如,会员所缴的货币实体有现钱、满钱、九八钱、制钱、钱票等等,它们均以“文”或基于文的“吊”为单位,形制、价值却有本质区别。那么,充当记账单位的“文”与各种实体货币单位的“文”到底是何种关系呢? 一般认为,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通行一种称为“京钱”的虚货币。
京钱起初只是京师所铸铜钱的简称,是实货币。清代京师有源泉二局,所铸钱比地方铸局标准,流布各地,在被称为大钱、制钱的同时,有时也称为京钱。咸丰以前,官方文献中出现的“京钱”,多是这一含义⑤。与此同时,民间又形成了一种虚货币,也称为京钱⑥。它的发生无从确考,据说源于康熙年间铸的小钱⑦。这样重要的制度或风俗,虽然进不了正史,但在稗史笔乘的传统中,得到了生动地记录⑧。而在描写嘉道年间北京世情的小说《品花宝鉴》里,能清楚地看到,实货币可以是制钱、钱票以及银两,但标价单位却通常是虚货币“京钱”。京钱不仅在京津通行,还延及河北、山东、东北等地⑨,国家图书馆及社科院经济所收藏的嘉道年间直隶宁津“统泰升账簿”就是以京钱为本位的⑩。
在华北、东北地区较流行的虚货币,除了京钱之外,尚有东钱11。京钱与东钱的价值都不及制钱,通常的说法是,京钱以制钱五百文为一吊,东钱以制钱一百六十文为一吊。由于这一原因,邓云乡将京钱的问题归结为铜钱流通中的“照例短陌”。不过,短陌主要是就通货或实货币在行用过程中的折扣而言的,可无论京钱还是东钱,它们都是不局限于具体行用的虚货币,所以将其视为某种短陌惯例有所不妥12。此外,短陌的折扣比例通常是固定的,如九八扣、七折等等,然而,下文将表明,京钱并不简单等于五折制钱,虚实货币若即若离,传统的短陌概念不足以说明其中的关键。
火神会账本并未注明其记账货币,但起初以五百文制钱为一吊,可见是以京钱记账的。不过,它在咸丰后又改以一百文为一吊,其原因或者是更改了货币单位,或者是京钱的价值由五百文制钱降为一百文。实际情形恰是后者。附表中摘录了账本所用的银钱比价,所获数据限于咸丰年间以后。可与之比较的银钱比价序列有河北定县调查辑录的银钱比价13、北平账簿中整理出的银钱比价14。这两组序列中的铜钱为制钱或铜元。以一枚铜元作十文制钱统一折为制钱表示后,定县及北平序列的银钱比价与火神会银钱比价基本上为 1∶ 10,而非 1∶ 2(见图 1)。笔者从“万盛木厂账簿”15算得 20 世纪初的银钱比价,高达十数千,与火神会账本一致。甘博在研究北京附近某燃料铺账簿时,也发现该账在 1860 年以后采用了新的货币本位,新本位的价值为原本位(五百为吊的京钱)的五分之一。16 所以,上述三种账本在咸丰以后都采用了新的本位,以一百文为一吊。
但是,该新本位其实仍是京钱。对此,清末民初的多种史料可为佐证。《清稗类钞》(“农商类·京师钱市之 沿 革”) 记 述 光 绪 庚 子 (1900年) 以前京师的货币行用时,提到“吊者等于南方之所谓百,一吊含大个儿钱五十枚”。其中的大个儿钱即当十大钱,实抵制钱二文,所以一吊当制钱百文。民国时期关于北京旧习的调查称,“制钱称为京钱,品质颇优,以每百文为一吊,普通商家概以吊为计算单位”17。从日升昌票号京师分号致总号信件中的相关资料,也能推知记账货币的变化。18 该类信件有报告京师钱价的惯例,道光末年系按每吊值银若干钱报告,为三钱上下;光绪十六年则按值银若干分报告,在七分左右。比照其它银钱比价数据,很明显,道光年间报价本位为五百当一吊的京钱,咸丰以后就是百当一吊的京钱了。19
京钱的价值又缘何落至百文呢? 邓云乡曾略为说明。20 其主要依据是《越缦堂日记补》关于票钱贬值的记载。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减值(debasement),而非贬值(depreciation)。因为它是本位币对实货币价值比例的调整,而不是简单的货币购买力降低。那么,一吊京钱是在何时、如何由五百文减值为百文的呢? 笔者大体赞同邓云乡的判断。在咸丰铸大钱以前,京钱是以制钱五百为一吊的,咸丰三年铸当十大钱以后,京钱渐改以大钱五十为一吊。由于当十大钱贬值,由折十减至折二,一吊京钱(当五十枚大钱)遂只值百文制钱。至于京钱减值的具体时间,甘博从他研究的账本推断是在 1860或 1859 年。21 火神会账本中的筵席价在 1861 年由每桌3 000文调整为15 000文,则该账的本位货币调整是在 1861 年。又,张集馨描述了咸丰四年以后数年各种通货“走马灯”般的乱象,混乱之中,京钱尚未减值已先贬值,及至咸丰九年,“五十金换京蚨七百串”,即银一两当京钱十四串,已经接近以百文为一串。22 所以,甘博推断的减值年份发生的其实是贬值。正式的减值是到咸丰十一年即 1861年才实现。此次减值的前奏是当年六月,官方决定清理官钱铺,同时强制民间钱铺重新发钱票,但是不与官票挂钩,“各开各票”。23 七月初,各铺陆续发票,按当时的市价,每千换制钱一百或大钱五百,24正式实行了减值,这与火神会账本是一致的。减值以后,货币市场逐渐稳定,京钱也就保持在以百为吊的水平上。不过,民国十年以后,火神会账本开始更多地以洋元为记账单位,京钱虽然仍做为一种虚货币存在,却已失去了记账本位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以百文为一吊”的表述并不严格。随着制钱、当十大钱与铜元的代起更迭,咸丰以后一吊京钱的价值经历了百文制钱、五十枚当十大钱、十枚铜元的变化。而当十大钱、铜元从重量和成色上本是对制钱的减值,继后且又因滥发不断贬值,所以清末以后的一吊京钱实际上远远当不了百文制钱了,制钱也自然要在市场上绝迹。25 图 1 以银两为标准,比较了充当记账本位的京钱与铜钱实体的价值变化。铜钱在咸丰初年贬值后又回复了,但京钱发生的却是难以逆转的减值,结果京钱与制钱间的常量关系被打破。清末铜元滥铸,京钱随之一道贬值,已然没有锚定于一定量的铜或标准重量与成色的制钱。如果说制钱仍具有金属本位某些特征的话,京钱就基本上不具有这方面的特征了。
彭信威非常精辟地指出,当铜元被接受时,传统的物价波动真正地转变为“物价革命”。26 那么,在京钱追随当十大钱并进行减值时,这个意义上的革命就开始了。
三、通货或实货币与虚货币的关系
京钱价值的变化体现了虚实货币间的辨证关系。一方面,虚货币脱胎于实货币,必随实货币而转移,如京钱的减值即对应着当十大钱的铸造。另一方面,虚货币是对林林总总的实货币的抽象,名义上更加超脱与稳定,各种实货币因而可以以它为换算标准统一在一起。
从火神会账本的收支记录中,可以略见近代北京繁多的实货币名目及其与京钱的关系。现列举实货币如下:钱、现钱、满钱、全钱、九八钱、制钱、票、九八票、制钱票、全钱票、现钱票、官号票、铜元、铜子、京松银(京平松银)27、交通洋元、现洋。民国九年以前出现的主要是各种钱及钱票,其中的票类比重有增长之势,在咸丰四年前后、同治末年、光绪年间比重尤大28,至宣统、民初则均为全钱票。官号票仅在咸丰十一年出现,该年的收支均按官号票记账,一吊仅值全钱六百29。制钱和制钱票在光绪二十年偶现,一吊值京钱三吊以上———这里的一吊应该只有制钱百文,即京钱一吊远远不值制钱百文了。铜元和铜子仅在光绪三十一和三十二年间使用。民国四年有一例交通洋元,民国九年后现洋成为主要的记账单位。
根据账本中的各种记录,所谓钱、现钱30、满钱、全钱之类,均与记账本位(京钱)等值行使。在铜钱行用中,实行九八扣是许多地方通行的惯例,北京也如此。账本中九八钱及九八票出现得尤其频繁,在同治年间,甚至记账、计价都往往采用九八钱。即使是在使用全钱计账的年份,也可以看到原始单位应该是九八钱。31九八扣作为一种短陌现象,如前所述,与京钱是两回事。不过,在京钱的基础上再行九八扣来记账,既佐证了京钱本身不是一种短陌折扣的判断,又说明实货币的短陌惯例也会影响到虚货币。另外,用票相对用钱(如九八票对九八钱、全钱票对全钱)无须贴水,证明钱票基本上能做到通行无碍。只是钱票以吊为单位,用于零星交易则颇有找零的麻烦,这在账本中也有所体现。所以,只有随着京钱的减值与贬值,火神会的香资交纳才越发使用钱票。
在各种实货币中,钱票值得更多地关注。钱票实质上介于实货币和虚货币之间。首先,它作为代用货币具有通货的功能,可视为实货币。其次,它本身不含金属,是符号化的,自然可以以虚货币为单位,于是成了虚货币的实际对应物32。换个角度来说,京钱这种虚货币的成立,是有钱票作为通货基础的———尤其是咸丰减值以后。如前所述,咸丰十一年京钱的正式减值就是通过各钱铺重新发行钱票来实现的。其实,咸丰大钱铸造量名义上虽有七八百万吊制钱33,但按实际价值仅百万余,其中铁大钱作废销毁了不少,制钱又被挤出流通不少,所以仅从铜钱的增长来看,难以支持京钱那么大幅度的减值或钱计价格的那么大幅度上升———除非实际货币需求剧跌,而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京钱的实际基础很大程度上是钱票而非铸钱。
那么,钱票的基础是什么呢? 钱票主要为私票,银钱业乃至各种商铺都可以发行。在发行过程中,没有发行准备制度,更无信息披露制度,主要的保证就是无限责任和多户联保。因此,钱票的基础全在商人的信用。加藤繁在论交子的起源时,称其与铁钱不便有关,同时必须要代表商人的社会信用已经成立34。钱票同样如此。而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票号,商人的信用大抵是地方性的,故钱票虽能在本地与现钱无差,异地却几同废纸35。自然,以此为基础的京钱也是地方性的本位货币。根据《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所辑各地情形,京钱通行地区包括华北、东北的近京津地区,这与各地商业联系紧密程度应该是一致的。例如,采用京钱记账的直隶宁津统泰升号,它的往来客户分布除本地外,也就沧州、兖州、德州、获鹿等数处,未出环京津地区。
然而,京钱本位的地方性并不意味着所属货币体系的地方性。其中,银显然是跨地区的货币。火神会的账本中用银(京松银)的记录虽然极少,但涉及金额稍大的火祖会,其收支记录就是银钱并重。
这与统泰升账簿的情形类似———小额杂货买卖多以钱为媒介,而铁货等大额交易用银的比重要大得多。36 如果说银携带仍不够方便与安全,那么会票(汇票)为跨地区交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尽管会票的流通性有限,但票号与钱庄向有联络,因此会票、银钱票以及现银、现钱之间的辗转并无制度上的障碍,区际和区内的货币流通构成同气连枝的格局37。至于铜钱,虽然携带相对困难,不过作为官方铸钱,它也是全国通行的。在某些场合下,便捷的洋银甚至还敌不过粗笨的铜钱。38 并且,从理论上来说,尽管各地的铜钱行用有五花八门的惯例,可由于基本单位相通,就为汇兑过程减少了一重风险———同时难免让货币兑换商少了一种套利机会。就此而言,官方对制钱制度的维持有助于实现地方货币体系的开放性,也有助于国内货币市场的整合。
在上述京钱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商人或民间信用、国家信用、币材天然属性及铸造技术是相交错的主线,共同决定该体系对交易成本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效率。39 在民间信用有效的情形下,钱票等信用货币能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而清前中期维持较好的国家信用使得笨重的铜钱在广袤的疆域内具有效力,从而为民间信用的建立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不过,如果没有白银这种天然更加便捷的贵金属的竞争,国家信用不会得到那么精心地维护———银钱比价几乎是朝廷最关注的经济指标,甚至超过了粮价! 可是,国家信用从来就不是那么可靠,特别是 19 世纪受到了种种冲击之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官方在对私票进行种种非难后,被迫仿效商铺发行钞票,结果其价值却比私票还要大打折扣。
咸丰年间官方的滥铸、滥发,还一度连累到私票。40 虽然通货膨胀推进了钱票在小额交易中的使用,但价值无法稳定却终究使钱票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大打折扣。及至银元引入之后,钱票的便携优势也不再明显,行用程度日趋减退,京钱的本位地位也随之日渐瓦解。
这样,在近代北京通货的变迁中,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信用隳堕、民间信用难以为继,结果银元凭借天然的优势以及舶来的铸币技术取代了京钱的地位41。这种白银独秀的方式未必就是进步,因为相比信用与良材交相胜的货币体系,它在解决交易成本问题上反而可能更缺乏弹性。当然,这方面的进一步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下文仅通过价格数据,试着分析币制变迁中北京的通货膨胀。
四、物价、工价与银钱比价
根据火神会账本的开支记录,可以计算出若干与祭祀活动有关的价格数据(参见附表),较完整的是筵席(账本中称为席、席面、席菜)价格。筵席价格系以桌计,决定该价格的因素有各色菜料的价格、燃料价格、厨师的工价、餐馆的商誉等等,包含了商品和服务两方面内容,具有一定的综合性。42
如折为银计,火神会席价咸同年间一两左右,民国后涨至二两外。该席价中未含主食及茶酒价,这部分不过席价的二三成。无论从价格还是色样来看,火神会的筵席尽管有堂字号代办的,却仍属简陋。按《清稗类钞》记述的光宣席价,数两至二三十两不等,如福隆堂、聚宝堂每席之费则为六两至八两。43由于清初席价不过数钱一两,晚清时人每叹人奢物贵。现在据火神会席价来看,纵使人不奢,物也是贵了不少的。例如,与乾隆初期所定则例中的六等席相比,火神会席远逊,至多不过其三分之一,价格却得其太半以外。44 从账本中还可知,道光年间馒头大概四五文制钱一个(每斤约十个),猪羊肉大概五分银一斤,无论按银还是钱计算,价格都比起清初有大幅上涨。45
当然,考虑到资料的可比性,上述比较仅是粗略的参考。更有意义的是与同时期其他价格序列进行比较。图 2 绘示了账本中的若干价格序列,并将它们与工价、苏松米价比较。其中,工价指数据甘博等整理的 1807—1902 京郊燃料铺非熟练工价和 1900—1925 北平瓦木匠工价衔接而成46,米价指数依据王业键整理的长江三角洲米价47。
图 2 首先表明了道光年间至民国十四年京钱的贬值与钱计物价、工价的上升。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商品的价格变化有局部的差别,但在受记账货币减值和贬值的带动方面,是一致的。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茶房酒资48与工价亦步亦趋,这证明了工价数据的代表性,给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提供了支持。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席价与工价,来观察相对工价的变化49。直到 20 世纪初,它们的上升步调都差得不大,只是工价的波动显得更微小。在 1910 至 1920 年间,筵席价格的上涨超出工价许多,几达四五成。到 1925 年,工价上调,开始追赶席价。如果考虑到 1930 年后食品价格的普遍下跌,那么工价很可能打了一个翻身仗。总体而言,在这百年里,工价与席价的趋势大致吻合50。R. C. Allen,J. P.Bassino and Debin Ma 绘示了近代北京工匠的福利指数( 主要基于甘博等整理的账本数据及李明珠整理的粮价单数据),表明实际工价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并无显著的趋势性变化。51 即便如此,倘若考虑到图 2 中 1910—1920 年间工价的远远落后,相对价格变化的总效应对劳工可能还是不利的。不过,以往只强调劳工因银钱比价变化而受损,则有失偏颇。
倘若把饭、馒头等谷制品归为一类,在咸丰六年后,它的价格就开始成倍上升,而记账货币的减值以及席价、工价的上升与之相比都晚了三四年52。直到 1890 年间,席价、工价似乎都未追上谷制品价格,说明粮食相对更贵了。其实,这段时期以银表示的苏松米价是颇为低迷的,那么,如果用银来标价的话,则应该说其它商品比粮食更疲软。1900 年前后,谷类价格与席价、工价等又走到一起,相对价格的结构恢复到了道光年间的状况。如果苏松米价的提示无误,那么,1910—1920 年谷类价格上升较多,并带动了席价同步变化,而 20 年代后谷类价格上升开始乏力,席类价格却继续走高,工价也赶了上来。解释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可以有多种———诸如人口、气候、时局等等,本文不拟探讨,只希望
通过图 2 说明,无论如何,价格结构的变化很难说有一个简单、恒定的方向,在进行解释时,需要更小心地选择时间尺度,或进行更规范的时间序列分析。
另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银计与钱计的价格。银计价格中,王业键整理的长江三角洲米价是最有代表意义的53,即图中名为“苏松米价”者。所谓“道光萧条”或者更长的、延至 19 世纪晚期的不景气,都可以从苏松米价的低迷中得到反映。但是,如果我们看北京地区的钱计物价,却会发现全然不同的面貌。而京钱又是北京地区通行的本位货币,于是,就会发现江南发生通货紧缩,北京却并未发生甚至还相反。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陈昭南引入货币区理论,将银钱比价视为用银地区和用钱地区的汇率54。与浮动汇率类似,银钱比价的波动起了防止通货紧缩或膨胀在地区间传染的作用。结果,主要用银的南方受银根紧缩的影响较大,北方受的影响却较弱。不过,上述推理也有与当时的实际情形不尽符合处。首先,在银根紧缩的同时,北京在获取铜的方面也遇到了困难。其次,银根紧缩导致了北京所能集中的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又会使得当地的银、钱两种货币供给都告萎缩。再次,在当时的南北经济格局下,北方似乎难以因南方通货紧缩而增加输出。所以,笔者认为,铜钱部门如何实现内生扩张对理解 19 世纪钱计价格的形势更为关键55。私票和私铸的泛滥、官方与学者对大钱寄予的希望,都可以从这方面加以理解,而未必给以全然消极的定性。
当然,铜钱部门扩张的效果并不理想。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物价上涨、京钱减值,大大抵消了货币供给实际额的增加,这使官方通过铸币税改善财政的企图落空,并意味着对国家信用有所凭恃的制钱制度也无法重建。二,铜钱部门的地方性与当时经济的跨地区发展不尽适应,它的扩张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地区内经济运行的需要,但对缓解银根紧缩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很有限的,从而对整个经济局面的作用也很有限。在地方不予配合的情形下,北京的政策甚至反过来使自己更加困顿,陷入滞胀之中。三,尽管在咸丰初年及光宣之际,价格波动的步调出现了不一致,地主、官僚以及商人可能会从价格结构的变化中获利,然而,是否能从这些“货币幻觉”、“价格粘性”的蛛丝马迹中推出凯恩斯主义所乐道的“通货膨胀———经济扩张”机制? 恐怕还很困难。例如,咸丰初年的工价调整虽滞后于谷制品价格,但并不滞后于席价,商人未必能从中牟利。反过来看,币制混乱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却有众多的史料为证56,某些善于投机的胥吏或商人或许因此得利,可是经济繁荣却并未伴随通货膨胀而来。
五、结语
火神会账本中留下了近代北京货币行用的一个剪影。将它与其它直接、间接史料相拼合,为解读当时的货币体系提供了切入点,让我们更真切地探究其面貌。在这个以虚御实的体系中,京钱为虚,银、钱、票为实。统一的虚货币削减了实货币纷繁复杂给交易带来的困难。其中,京钱与钱票都是在民间行用过程中形成的,银基本未脱贵金属商品的性质,制钱则体现了金属天然属性与国家信用的共同作用。咸丰年间的滥铸滥发,导致制钱制度崩坏,京钱也由吊当五百制钱减值为一百。最终,在 20世纪初,钱失势,银元成为新的本位。
京钱减值后继续贬值,账本中的价格体现了这一通货膨胀过程。结合工价数据,可以看到在通货膨胀中,某些时段工匠的福利受到了损失,但就整个时期而言,很难说价格结构的变化有显著的倾向性。在钱本位地区发生通货膨胀的十九世纪,银本位地区却经历了漫长的通货紧缩。但是,本文认为钱本位的北方并没有摆脱厄运,依靠传统方式进行的铜钱部门扩张没有带来经济繁荣。事实上,银元的最终胜出就证明了铜钱部门内生调节的失败。
注释:
①具体为:“恭庆火祖会账本”,14 册,索书号 154206;“火祖圣会银钱总账”,2 册,153598;“火神会簿”,1 册,153599。除“恭庆火祖会账本”中的“出入银钱老账”一册及“火祖圣会银钱总账”二册属西单牌楼火祖会外,余十四册均为火神会账本。故以下统称火神会账本。
②火祖或火神的祭祀由来已久。《礼说》卷 10 有云,“帝喾有祝融,尧时有阏伯,民頼其徳。死则以为火祖,配食火星。周之司爟,实掌其祭以报其功。”又,《日下旧闻录》记载了明清北京的数处火神庙。
③这也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如乾隆年间的小说《歧路灯》(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六十九回,“盛希乔道:‘……这一千两,是我昨日揭到关帝庙山陕客人积的修理拜殿舞楼银。每月一分行息,利钱轻。原只许他山陕社中人使着做生意,我硬要一千。比不得满相公揭的,左右是三四分行息。’”
④国内的经济史文献提到虚货币的并不多,有所涉及的主要也是规元等虚银两———如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 民 出 版 社 1985 年 版,第 184—187 页 )。 在 国 外 的 经 济 史 及 货 币 理 论 研 究 中 对 它 却 颇 为 重 视,其 名 目 亦 有 多 种,如:monetanumeraria、moneyofaccount、idealmoney、politicalmoney、ghostmoney。 参见 Robert J. Shiller,“Indexed Units of Account: The oryandAssessmen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http:/ /cowles. econ. yale. edu/P/cd/d11b/d1171. pdf. )。
⑤咸丰以后,官方难以维持制钱制度,虚货币京钱因此也更多地进入了官方的正式讨论。
⑥下文所称“京钱”如无特别说明,即指虚货币“京钱”。
⑦钟大焜“拟请变法铸钱议”称,“本朝亦曾铸康熙小制钱,今所名为京墩者也。其重自八分至一钱而止,本以二文作一文之用。今天津为京钱二百,实只制钱一百,犹其遗意也。今则此钱散行各省。”(《皇朝续文献通考》,卷 21,“钱币考三”)至于虚实货币间的蜕变过程,从中亦无法得知。
⑧参见邓云乡《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 年第 4—5 期。
⑨如河北完县、广宗、山东馆陶等。参见戴鞍钢、黄苇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 年版)九“货币沿革”中,河北、黑龙江等省的有关条目。
⑩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8 页注 3)指出“宁津县计算钱文,两吊为一吊,二文实一文”,与京钱同。又据注 8 的资料,在当地这种计算货币即唤为京钱。笔者曾翻阅“统泰升账簿”(国家图书馆藏),发现记账货币一般仅称为“钱”,少数情况才特称为“京钱”,道光后期还有部分明细账用“大钱”也即制钱为单位,“钱”与“京钱”等值,为“大钱”二分之一。“京钱”而非“大钱”直接简称为“钱”,可见京钱才是具有一般性的本位货币。
11参见《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九“货币沿革”中,河北、奉天、黑龙江的有关条目。
12短陌现象文献中并无明确的解释。或以为是“朝三暮四”的恶俗(《梁书·武帝下》),或评为畸形紊乱的封建币制之表征(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 1986 再版,第 48—49、61—63 页)。在笔者看来,只不过是现实的商业世界远比逻辑推理的复杂而已。例如,现在的度量衡是高度统一的,但在内地的集市上,鱼行有带水之例、鸡鸭行有带食之例、菜行有带土之例,种种斤两的折扣,不一而足。从经济学上来说,出于特定交易中“菜单成本”、“歧视定价”等方面的考虑,计价单位的调整时常会比价格本身的调整更可行。短陌惯例的形成也应如此。至于虚货币的选择,却关涉币制,而不局限于具体的交易过程。
1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民国丛书》第四编影印自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33 年版,上海书店 1992 年版,表 295。
14Meng,T. P. and Gamble,S. D. ,Prices,wages,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Peking,1900—1924,Peking Express Press,1926.
15万盛木厂“伙计支使账”,北京档案馆藏,J93—5;万盛木厂“王宅用工料账”,北京档案馆藏,J93—7。
16 Gamble,S. D.,“Daily Wages of Unskilled Chinese Laborers 1807—
17 《中国重要都市通货之现况》,《中国经济周刊》1926 年 7 月第 169 号,第 1—12 页。该表述存在概念上的混乱。它所称的京钱是作为实货币的京局铸钱,而后面“每百文为一吊”,谈的又是虚货币,该虚货币也是京钱。
18 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下部第一编之第一、四、五、六各章所辑京师分号发出的信件。
19《山西票号史料》表 2—1—11 注二(第 1105 页)认为,光绪年间京钱仍然是五百当一吊。这样,银钱比价显得太高,所以原件中本来是值银若干分的,该表却改为若干钱。如果接受咸丰年间京钱改为百当一吊的判断,那么原件中的“分”是正确的,不应径改为“钱”,而且与道光年间的报价也衔接得上。
20邓云乡:《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 年第 4—5 期。
21 Gamble,S. D.,“Daily Wages of Unskilled Chinese Laborers 1807—
22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51、267 页。
23参见《咸丰十一年六月戊寅上谕》,《清文宗实录》第 355 卷,第 10—12 页;咸丰六年管理户部事务周祖培等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 1 辑)》,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478 页。
24参见咸丰六年管理户部事务周祖培等折(《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 1 辑)》,第 478 页);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 3 册,广陵书社 2004 年版,第 1861 页。
25如民国二十二年《广宗县志》所载河北广宗的情形,“自清末改用铜币,制钱绝迹,惟计算时仍以当十铜元五十枚为一吊云。” (《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 1053 页)
2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3 版。
27山西票号来往信件中提到的北京银色有松江色及九九色两种,则“京松银”及“京平松银”意为京平松江色银。见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41 页。
28从账本记录来看,票钱及九八钱的基本单位为吊。而会费常有零头,特别是咸丰初年前还不足一吊,所以该账对票钱重要性的反映相比当时的普遍情形尚有所不及。
29据《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一年六月,票钱一千换制钱在六十文上下,
30这里的现钱应该是相对质量较好的老钱而言的。如济澄“请饬查禁钱店舞弊疏”提到,“以银易钱,又有老票、现钱票、原串之名,每两易老票只在十千以内,现钱票则十二千有零,原串可至十四五千。”(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 8 页)
31如同治元年账上每号香资全钱 1 960 文,实际上是交九八钱二吊,折以全钱记账。这种例子颇多。
32如,在统泰升账簿中,用银交易的都要注明平、色、类型,而用钱交易的极少提到小钱、几扣之类的,只见若干帖、兑及现钱等注,若非是通用与记账本位一致的钱票,这是难以解释的。又如,《品花宝鉴》第二十三回,李元茂嫌钱难带,将五吊大钱在烟钱铺换了十张票子,即是以京钱一吊为面额的。
33参见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34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4—5 页。
35当然,钱票的有效范围还视商业网络状况、习俗、发票方信用等而有别。如黑龙江的钱帖,又称街帖、屯帖,顾名思义,仅限街屯之间(《黑龙江金融志》第 1 篇第 2 章第 1 节,http:/ /www. zglz. gov. cn/trsweb/Search. wct? ChannelID = 3116)。此外,京师钱票限于京城使用,安徽滁凤芦颖诸处钱票,则可至二三百里外取钱(王鎏《钱币刍言》,艺海堂藏版,第 312 页)。但总体而言,其地方性仍是不可否认的。
36参见统泰升历年之出入账簿,国家图书馆藏。
37近代各种信用工具的现代解读,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中研院经济所民国 70 年版。至于会票与银钱票的关系,可以分三个方面来理解。一,行用范围互补———“今京师民间贸易皆用钱票,远方商贾皆用会票”(王鎏《钞币议》,《皇朝经世文续编》)。二,功能不同,“钱票有辗转相授不取钱者,银票虽存本取息,亦须岁易其票。若会票则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空票”(许楣《钞币论》,古均阁版,页 15 许槤评语)。三,互相渗透———“京师交易由于钱店,钱店之懋迁半出账局(引注:主要指票号),而账局之放贷全赖私票”(咸丰三年宝钧奏折,转引自《山西票号史料》第 45 页)。
38沈复《浮生六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1 年版,第 84 页)提供了一个例子———“临行以番银二圆为酬,山僧不识,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钱七百余文,僧以近无易处,仍不受,乃攒凑青蚨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谢。”按作者生平推测,此事发生在乾隆末年。
39显然,笔者不赞成阶段论式的货币发展观。Boyer-Xambeu,Marie-Thérèse,Ghislain Deleplace,and Lucien Gillard,Privatemoney &publiccurrencies:the 16 thcentury challenge( N. Y. :M. E. Sharpe,1994. ) 关于 16 世纪西欧货币体系与现代货币共性的反复强调 ,将货币体系划分为贵金属(对应国际贸易)、汇票(对应西欧贸易)、铸币和债券(对应国内贸易)三个层次的做法,用到近代中国并无不妥。
40参见前引魏建猷著,第 91—92 页。
41顺便指出,这里不宜泛泛使用劣币、良币的概念以及格莱辛法则,因为劣币和良币都是根据市场价值与规定兑价间的关系确定的。在某些场合下,大钱、钞票相对制钱或许还可称为劣币,而由于银钱比价的灵敏,白银尽管具有携带方便、避免政府机会主义等优点,却不是格莱辛法则意义上的良币。
42火神会账本记载的筵席,每桌大致六人,食物含猪肉、羊肉及蔬果,主食和茶酒以及烟等一般另算。笔者估算的结果是,每人约可分得肉类一斤,主食(主要为饭)半斤。
43《清稗类钞》“饮食类·京师宴会之肴馔”、“饮食类·京师宴会之八不堪”、“风俗类·以物价觇俗”。
44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154“光禄寺·颁胙祭”,满六等席价银二两二钱六分,用面二十斤,红白环馓三盘,棋子二椀,麻花二盘,饼饵十有二盘,干鲜果十有八盘,毎席并用熟鸡或熟鹅一只,另有酒茶。根据火神会账本道光后期的记载,一斤肉价当二三斤馒头价,则火神会每席席面与主食等合计不过与六等席的面食相当。又据该账,道光间面每斤不过三分,则乾隆六等席中面价比例定不过三成。
45据《野叟曝言》第 18 回、《儒林外史》第十八回有关描述估计,清初馒头不过二三文一个。由龚炜《巢林笔谈》“顺治三年席费”所记物价、钱价,康熙中期猪羊鸡鸭肉约二分多一斤。
46 Gamble,S. D. (1943),“Daily Wages of Unskilled Chinese Laborers 1807—
47 Wang,Y. C.,“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1638—
48账本中称为茶师傅酒钱、茶房酒钱。从账本的记录可以发现,“小菜”一项的支出与它完全一致。所以,在该项未记录时,即补以“小菜”项下的数据。
49万盛木厂“王宅用工料账”中的木作、瓦作和夫价体现了同样的趋势,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上涨,1930 年时达到宣统民初的二倍。在考察 20 世纪最初 20 年相对工价的变化时,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一,20 年代以前,小工价或夫工价的上升幅度比木瓦匠要弱得多;二,工价的调整要经过行会,并不灵活,只能在较长的尺度上(如 10 来年以上)用来说明供求的变化。
50当然,这个判断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如果这个百年只是一轮更长周期的一部分,那么,只有将 18 世纪末以来的序列拉出来,或许才能有更可靠的结论。
51 Allen,R. C. ,J. P. Bassino and Debin Ma,“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and Europe,1738—
52原因之一或许是大钱驱逐制钱,导致零星交易面临困难,升米棵蔬之类的价格率先受到大钱的冲击。如吴廷栋《陛见恭纪》(《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49 户政二十六钱币下”),“今市中但见大钱,不见制钱,小民实是不便。穷民日用零星之物仅值数文,即物价亦必有奇零,市上只有当十大钱,并无当一制钱,岂非不便? 今百物腾涌,实由于此。盖官以一钱为当十,民以当十为一钱。”
53关于该米价序列对全国粮价的代表性,参见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二、三章。
54 Chen,C. N.,“Flexible Bimetallic Exchange Rates In China,1650—1850: A Historical Example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 7,No. 3( Aug. ,1975),359—376。
55 参见前引彭凯翔文第五章的有关讨论。
56 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 2 章、前引彭泽益及张国辉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